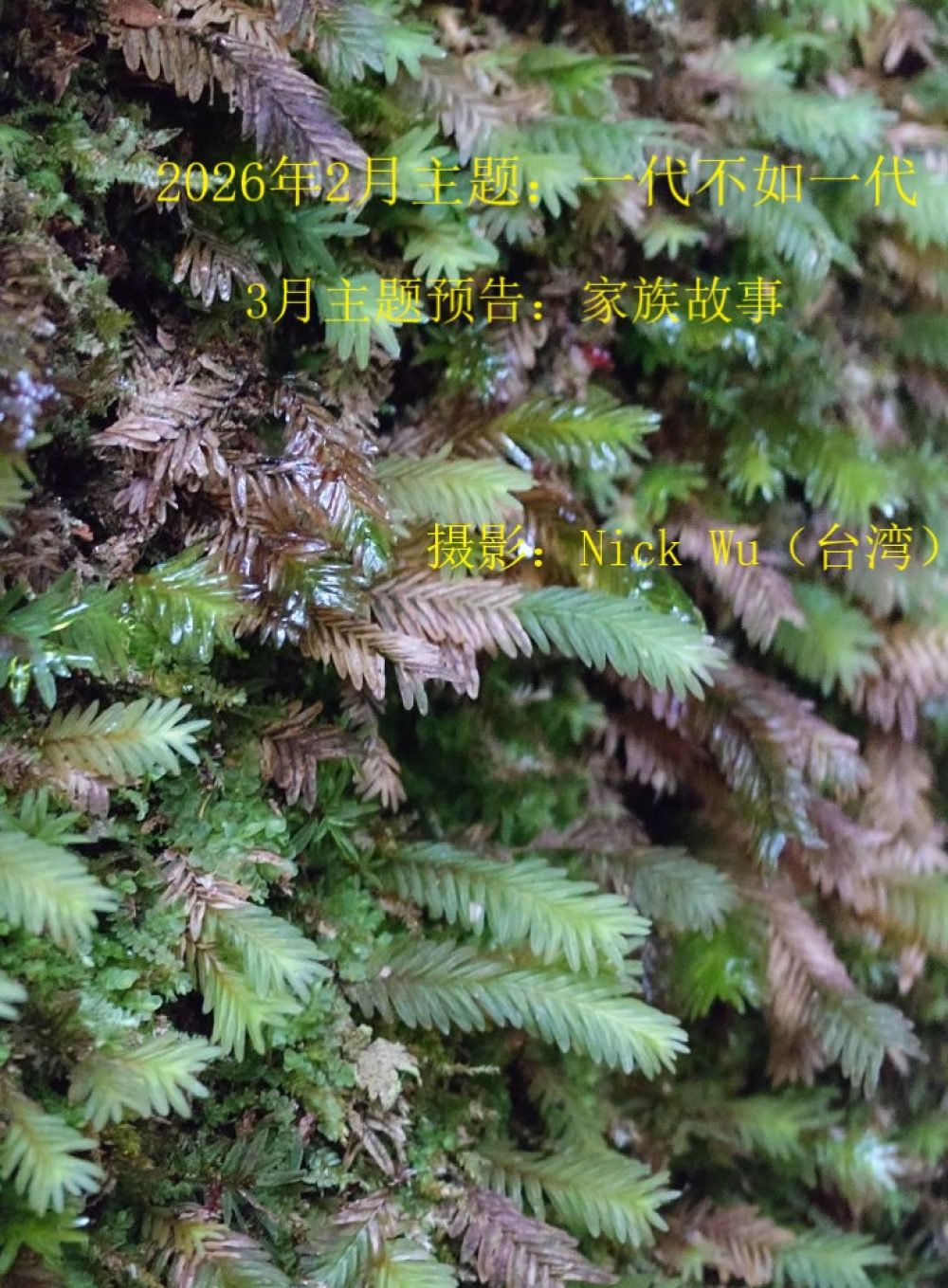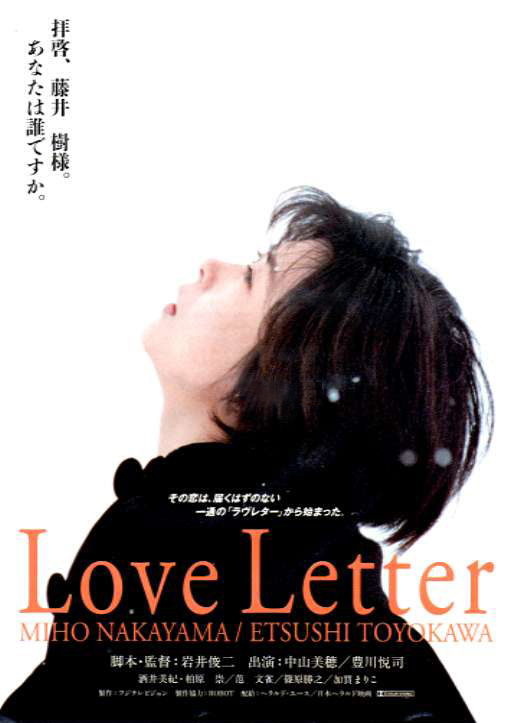这世上,能攥着人心的事物太多了。有人对声音着迷,有人对爱情着迷。着迷本身就有种玩物丧志的负面印象。当然,这年头,有赚钱的本事就能洗脱丧志的嫌疑。玩电动就是最佳例证。没对任何事物沉迷过的人,本质上就缺乏对人事物的热情。这种人,我觉得一定是很无趣的。然而,沉迷、耽溺和狂热都不可量化,彼此各自为营。最终,能小资情怀地赚点钱的那些人,大概都能让人谅解,甚至赞誉。
数学,曾经让我着迷,觉得很快乐的。高中时期,我喜欢独立思考,在数学老师对数理解释的范畴之外,闭门造车,用不同的方式解题,常常觉得有种自足的快乐。当时候国中的课程相对轻松,我却常常旷课。喜欢在无人的野径上独行,作无人审阅的习题。然而,这种快乐如秋蝉一般,在最自在欢唱的当儿,却没意识到冬寒的变化,一响贪欢。
中六,我选修了双数学。人往往对重大的灾难总是后知后觉的,正因为轻心大意,这才酿成这种“汉卿误我”之慨。如果说人生是一棵树,每个日子就像一片片的树叶,每一片都独立但又有近乎的茎脉纹理;那么,中六那段时间就像西山雪片一样,大如织席的雪片罩在脑门上。忽然,所有的数学方程式变种,成了最难缠穷凶恶极的魑魅。首先,误坠红楼,已经预先收复了我多年积攒下来的所有闲暇。再弄个穷追不舍的变形数学,我忽而变得穷于招架,像卑微的小卒,衔枚疾走。但闻人马之声,不暇顾。只觉得数学忽然不再是熟悉的数字,几乎都是英文字母串成的演绎。没有应用的纯演绎像在御劲草而行、踏凌波之微步,无一处可借力使劲。凭空挑刺,金戈铁马,我这穷兵弱勇,舞不起这定海神针,注定败北。
这才意识到数学之险。在几近没顶之灾中活着,从此不敢再语数学。它确实攥着人心。多少年以后,多少个夜晚还会惊醒,梦回当年临考前夕如临深渊,步履春冰的恐惧。这多少叫我也体会了李后主亡国之痛。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在梦中的考场,也确实是这么一番景象。
而今,数学又成午睡的良驯小猫了。在日常生活中几乎都是真实数字的应用。酒瓶子的数量、钞票的面值、午饭的钱、上个月信用卡的账单等等。那些个噩梦也还做,醒来看看熟睡的太太,忽然大悟。当年一役,我手擒数学之母——当年数学最好的同学,为压寨夫人十余载,不定,算起来还略胜一筹。
心喜,遂安。
摄影:PL Tan (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