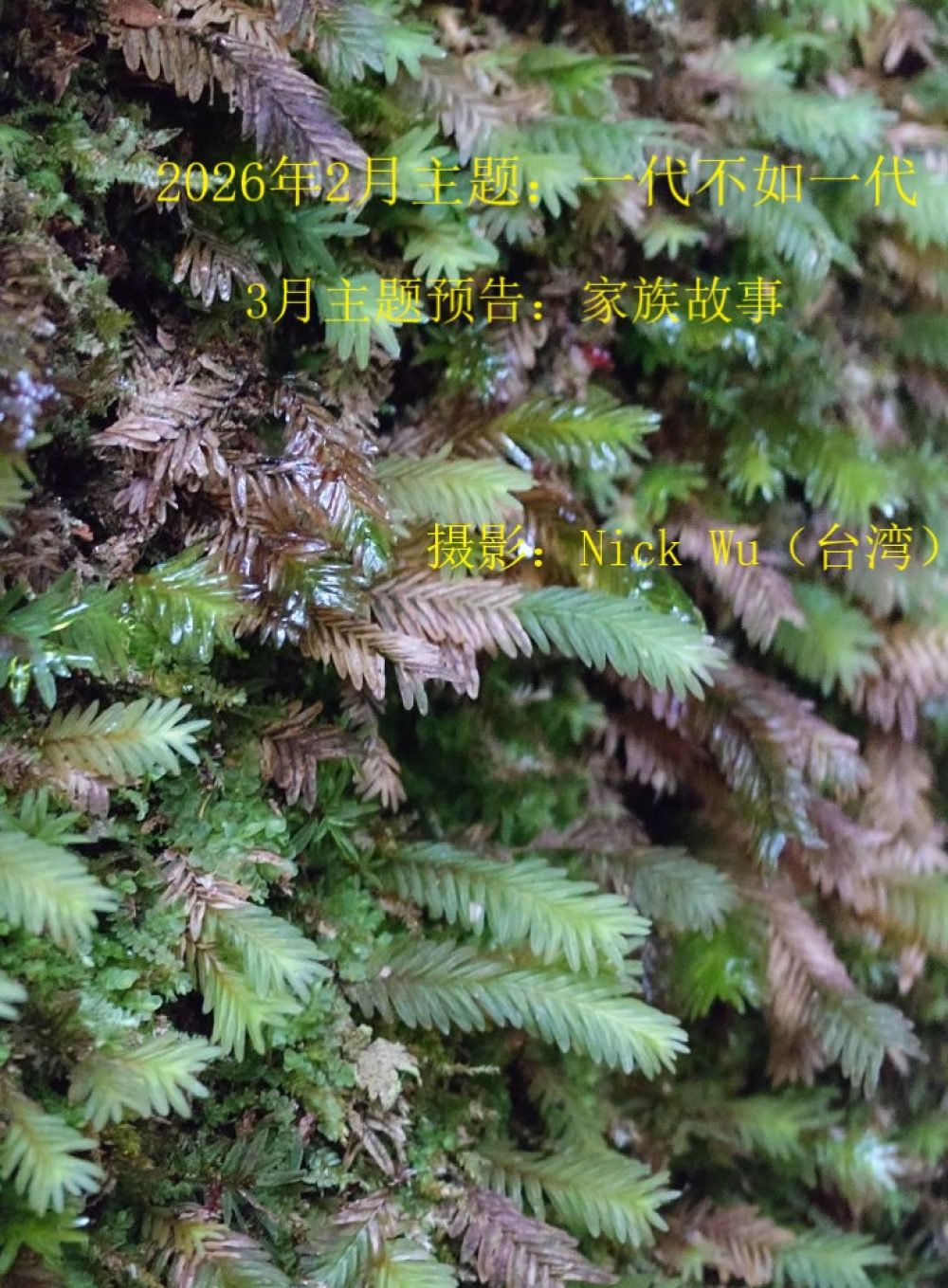尽管才诞生短短几十年,“New Age”这个不甚响亮的名字,已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泛滥。它的发展首先得益于科技带给音乐的无限可能。上世纪60年代已经发展较成熟的电子合成器最先在西方乐坛流行。电声乐器的音色非常空虚飘渺,能带给人具象之外的无限遐想。同时产生的音乐多是各个音素自由组合,没有鲜明的旋律感,令很多人醉心于这种特殊的非原声乐器。
New Age致力于表现安静、平和、闲适的音乐,从诞生初确定的目标就是要逃遁现代文明的压迫和苦闷,因此很多新世纪音乐家都把目光聚焦到中国。泱泱大国,五千年历史中蕴藏的盎然古意恰好暗合了他们追求的音乐意境。我们熟知的有德国Karunesh的《Zen Breakfast道禅》。不过也许与他在的亲身游历有关,这张专辑听来虽然顶着中国佛道的帽子,却披着印度冥想音乐的外衣。另外还有同样负有盛名的Oliver Shanti的《Tai Chi 太极》系列。这类音乐在风格上其实都更趋向于World Music的类型,他们更注重的是东方民风与西方元素的水乳交融。
相比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知半解,日本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似乎更能深刻地理解汉风唐韵之魂。他们作出的中国音乐,才真正的达到形神兼备。这种新的音乐类型最大的贡献,便是使日本不再屈伏于音乐国度的边缘地带。如今,它不仅是亚洲的New Age中心,在全世界也有着让人侧目的地位。同时,日本新世纪音乐的巨大影响还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及邻国的电视、电影、动漫以及广告等各个产业渗透,被大量采用为电视节目的BGM,以及电影、电视节目的主题曲,使很多观众在看节目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被吸引。在日本,这群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喜多郎与坂本龙一。
喜多郎对电子合成器的兴趣来自于70年代末期的德国乐队Tangerine Dream,影响之大直到贯穿其一生。1980年与NHK合作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后来出版专辑《丝绸之路三部曲》)在喜多郎的创作生涯中是第一个高度。他在工作室里仅靠拍回来的画面素材完成配乐。弥散在片中的配乐不再沦为画面的从属,富有幻想力的电子迷幻风,让人不由坠入遥远而神秘的西域。紧接的《敦煌》和后续几张专辑,风格上与《丝绸之路》(音乐链接:按这里)大体一致,可以作为喜多郎早期作品的代表,即纯粹的电子器乐风格。
90年代喜多郎移居美国,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开始尝试嬗变。例如表现日本本土文化的《古事记》,就加入了以前不常用的传统自然乐器(如太鼓),加强了编曲的节奏感。90年代末期的《疗伤森林》、《大地之母》几张专辑曲风上较以前更平和,不再刻意放大音乐中的朦胧色彩。2000年喜多郎再次配合日本广播公司的纪录片《四大文明》创作了《远古》。配合纪录片环境背景,专辑还融入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民乐风格,以及自然声响。音乐依旧出彩,甚至在耐听度上超过当年的《丝绸之路》,可惜并没有达到《丝绸之路》的轰动。
喜多郎和班得瑞(Bandari)是一组反义词,前者总是努力用自然声效带你进入真实的瑞士山林,后者则一直用空灵的音符引诱你随他去一个虚无空间。但那不是对电子技巧的卖弄,他要表现的,仍是真实世界的情感。喜多郎把中国文化作为终生创作的根源,对古老文明一直抱着敬畏而虔诚的态度。我们可以从那自然流淌的音律中感受到他对宗教、对世界、对人性的深刻冥思。
坂本龙一代表了New Age的另一极。他的中后期作品将爵士、摇滚、治愈系等各种音乐类型融会贯通,从而走上一条更国际化更宽阔的道路。但和喜多郎类似,他也在同一时期受到西德电乐的影响。他的电子音乐成就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YMO成员的创作,另一个则是在电影配乐上尝试,其中以大岛诸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电影链接:按这里)最为出色。电影中主要的配乐乐器仍是单一的电子合成器。坂本龙一的电乐有着和喜多郎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喜多郎是奇异神秘,坂本龙一是哀婉清绝。在影片开头,主题旋律《Forbidden Colours》(音乐链接:按这里)以一连串跳动的音符淡入,直捣人心。渲染了故事背景的萧瑟、空旷。在叙事进程中,关键情节出现时,音乐总会适时溶入画面,以较急促的变调来烘托紧张的气氛,以乐曲的重音体现人物心理的震颤。在末尾的的场景,Yonoi割下Jack一缕头发,此时背景声是提琴搭配电乐。提琴在西乐中是很直观的乐器,细腻低沉的大提琴弦音,正适合表现悲怆凄美的感情。反复的旋律仿佛人物的独语,让人直接窥视到人物内心的游移、隐忍和无限哀伤。随着Yonoi的离去,琴音消失,以音量渐大的电乐带入高潮。冰冷的合成器音质,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契合。
除了《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坂本龙一还有一部成就卓著的《末代皇帝》(主题曲链接:按这里),这帮他拿了奥斯卡奖。但喜多郎仅有的两部电影配乐也完全能与之颉颃。一部是1992年美国导演奥立佛·斯通(Oliver Stone)的《天与地》(Heaven & Earth,主题曲链接:按这里),另一部便是1996年香港文艺片导演张婉婷的《宋家王朝》(主题曲链接:按这里)。《天》和《宋》是是喜多郎到达的又一个巅峰。各个主题乐在编曲上十分相似,每一首配乐的旋律又极佳,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喜多郎颠覆以往作品的风格,合成器的地位在弱化,如泣如诉的二胡、纯净的钢琴以及婉转的小提琴、清脆的扬琴,这些元素的加入使得他的作品更趋多元。
这三部电影的题材有些相像,都是讲述战争或动荡时局中的个人命运,因此三者编曲也有明显的共同点:即用气势恢弘的西方管弦交响乐来凸显乱世的悲壮,同时又用东方乐器的细腻温润渲染情绪的细节,两者和谐的交融在一起。坂本龙一曾在2001年将《末代皇帝》重新编曲,完全由古筝和笛子合奏,收录在姜小青的专辑《悠》之中。在我国的一些小型唱片公司发行的乐器专辑中,也间或出现上述电影的主题曲。这类翻奏通常仅选用一两种民族乐器,独奏或合奏,在音域上更清澈透明,但力度薄弱得多。如果放进电影,就没法配得起气势磅礴的画面。所以说,中西结合有时候才是最完美的选择。
简而言之,日本New Age的巨大成功体现在流行与艺术的并重。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过分理智,它追求旋律的美感,也追求现代化的音乐表现形式,而这些都是吸引现代人的最好标签。New Age也许不能称为庸俗的流行文化,但很显然它是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它自身的特质使得他有很广阔的群众基础,所以不用担心它曲高和寡。也许,New Age的意义,就是要告诉我们流行不一定不能代表经典。只要是细腻的韵味和丰富的情感,总是会带来深深的震撼。
摄影:Nick Wu(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