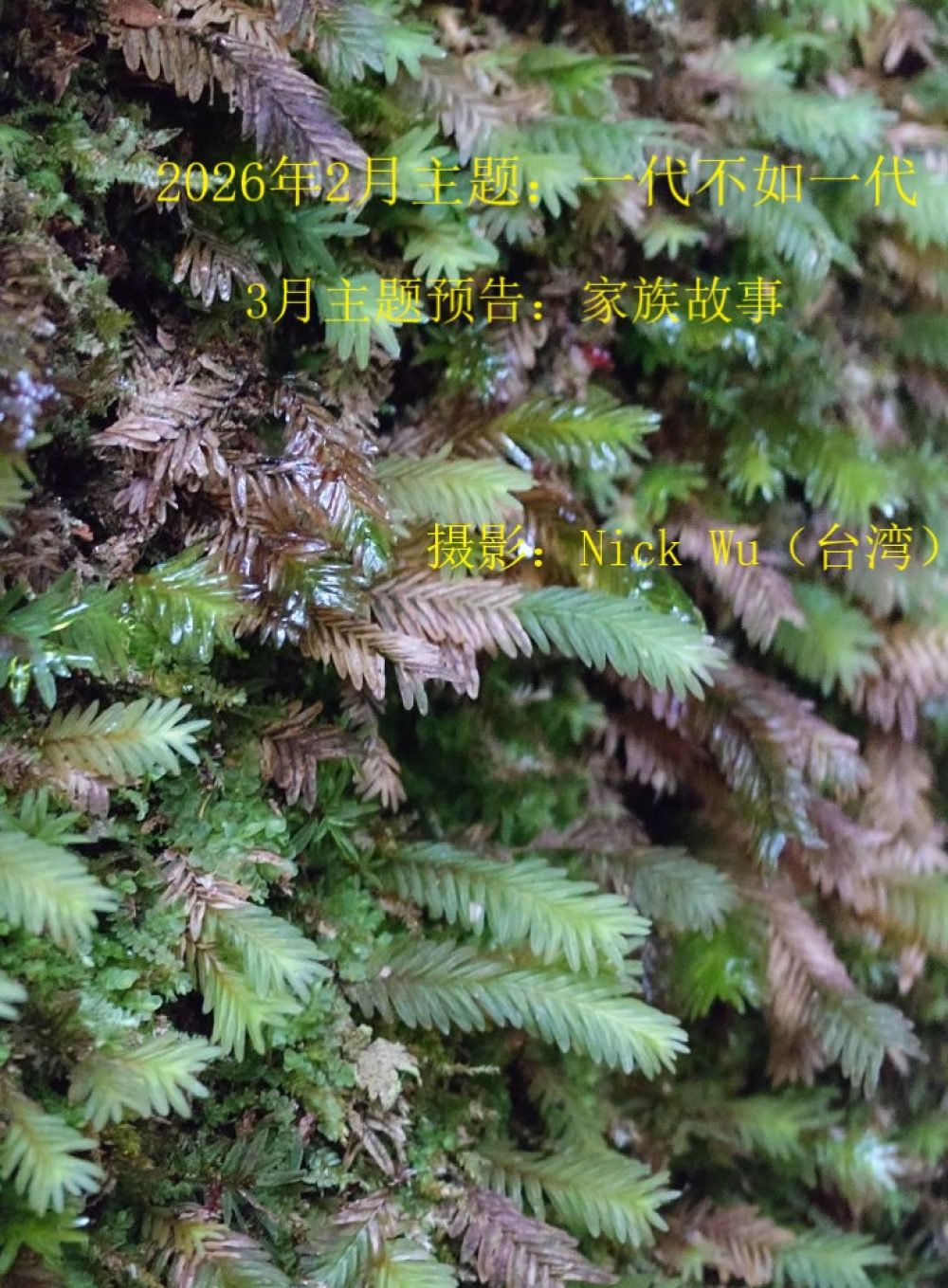望着灰色天空漫舞的雪花,总觉得应该想起一点什么来……
二十多年前,也是个下雪天。刚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让他靠着被子、枕头坐一会儿,喝几口开水。我刚想离开房间去准备午饭,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把我叫住了。他摸索着从里床边摸出一只残破的黑塑料包,翻出了一叠叠的纸片。
“这是我一生的档案,用不用得着,你自己看。”父亲把一叠大小不等、已经发黄的纸片交到我手里。我翻着要看时……
“你下次可以看,我先把这些都交给你。”说着,父亲又把比较厚的一叠大小不一鼓鼓扁扁的信封交给我,我一看就明白,信封上是我的名字。这是他的发小,香港的堂兄改革开放后通过我给他转寄来的信和照片。
最后,他拿出一个中号信封,抖抖索索地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了一叠银行存折。
“这里一共是七张存折,给七个小佬(编按:浙江方言,“小鬼”的意思)的。”接着,父亲把空塑料包也交给了我,又补了句“没有了。”说完,父亲闭上眼睛,身体靠到了后背的枕头上,仿佛放下了一个大包袱,透出了一口气。他把心灵的窗户关上了,我不知道窗户里面是悲哀、心酸,还是一点点自我安慰?
七张存折的名字分别是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七个孩子,他有三个孙子、两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她给七个孙辈每人存入了500元。从第一张存折到最后一张,时间相隔近十年。
父亲是1977年退休的。退休工资从当时的46元左右一直到1998年的400多元。七张存折交到我手里是1992年年底。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存起了这3500元。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了比父亲早逝十年的母亲。
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因为当时她生病,便没有了工作。那时没有社保、医保。她没有任何收入,虽然我每月给她20元零花钱,但吃饭还是要靠父亲。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去龙翔桥25平方的蜗居里看望父母,父亲不在,母亲就数落起父亲,并要我去问父亲一个问题。
“你去问问老东西,他的工资用到哪里去了。要他买条鲫鱼吃吃,他就是不肯。”
我说,我给你钱,你自己去买一条吃就是了。但是母亲不肯,她就是要知道父亲的工资是怎么用掉的。
去查问父亲的用钱,可不能随便问话。逮着一个机会,我问父亲:
“爸爸,你每个月工资,两个人够花吗?如果不够,我再给你点。”
“够哉。”父亲不会跟我多说一句话。我只能又问:
“那,有多吗?”
“有一点。”
“多下来干嘛?两个人用用完,用得舒服点。”
“我给每个小佬存点钱。”
我一时语塞,接不上话来,太意料之外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被评了一个资本家的出身。但其实他没有资产。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大伯拨了一部分定息给父亲。加上他的工资,每月也只有一百多元的收入,除此以外,没有房产、没有存款。过了文革,更是只剩下每月60多元的工资收入。我无法理解他给七个第三代每人留500元存款的心理,是遗产?是纪念?是做爷爷外公的意思、意思?
当我把父亲的这个攒钱不用的实情告诉母亲时,母亲沉默了。最后只说了一句:“这老东西,一句也不跟我说。”
直至1989年母亲离世,她从此再也没有抱怨过父亲一句话。
1998年秋,父亲离世。我履行父亲的遗愿,把七张孩子名下的存折交到孩子们的父母手中。本金500元已经变成700——900元不等值的存款。我不知弟妹们代孩子拿到这张存折有否回想、联想这笔钱的来源及其攒钱的过程。要知道这笔钱是父母双亲省吃俭用,从他们嘴里扣下来的吃饭钱,是用当时银行每月2元、4元等不同的贴花,年终兑现金的有奖储蓄积攒起来的心酸钱。
父亲自1956年,从他哥哥手里分得一点利息后,当了将近十年拼股老板的资本家,最后用自己的工资,从1977年起积攒了一笔3500元的遗产,留给了七个孙辈。已经成家立业的孙辈,是否解得老一辈赚钱的个味?
-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 主题:遗产
- 上一篇文章链接:我和孩子的约定/林明辉(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