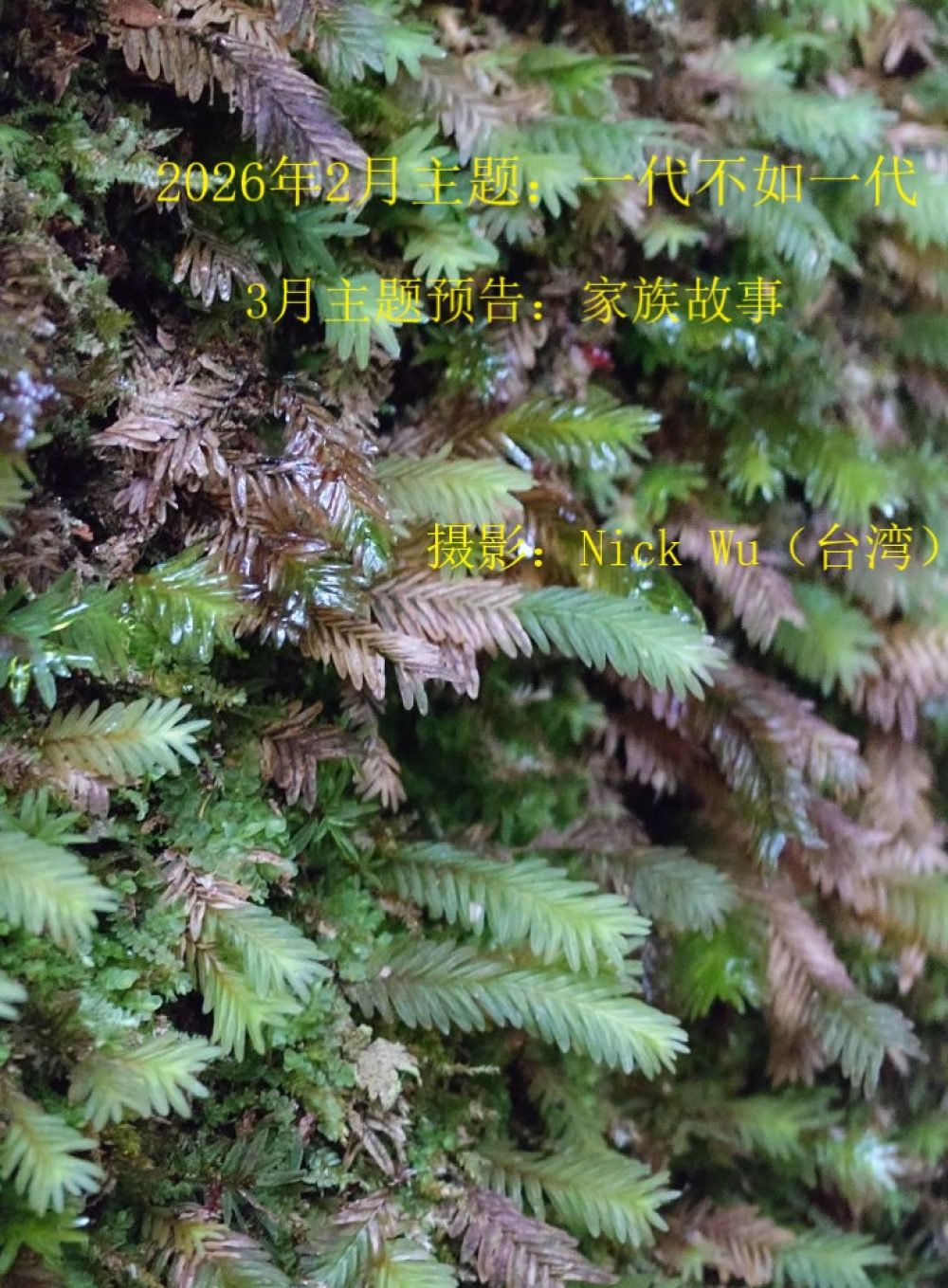对于远在异乡的游子来说,对故乡的思念经常会浮上心头。不过,你所思念的故乡,究竟是那个实实在在的故乡,还是只不过是一个抽象意义的、经过了你无数美化的故乡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围城外的人想进去,围城里的人想出来”,这句话对于故乡而言何尝不是如此:远在异乡的时候思念故乡,可一旦回到故乡,回到阔别多时的老家,过不了几天你又想回来了。大概对于很多回老家过年的人而言,这种体验再平常不过了吧?
我的老家是一个远在东北的十八线小城市。平时在南方,每当夏日潮湿的气候,就会思念起故乡干燥凉爽的天气;每当吃饭的时候,就会思念起故乡的美食;每当遇到一连下好多天、断断续续的霏霏阴雨,就会怀念故乡一阵冷风、一阵阴云之后霹雷一声下起的瓢泼大雨而这雨在几分钟瀑布般的狂泻后一定会停;每当冬天阴冷潮湿的空气降临,同样也会思念起故乡的鹅毛大雪以及雪后清晨一望无际的银白色……总之,一切不开心、不如意的情绪,一切困难艰苦的时刻,都会带来浓浓的、沉郁的思乡之情,乡愁永远是一个最容易最舒服的逃避场所,仿佛回到家里就没有这么多忧愁烦恼的叨扰了。
然而每年过年回家,现实则总是在证明一件事:故乡的美好半是你想象出来的,半是你人生前十余年的习惯使然。家乡夜晚寥落的街灯会让你又记起大都市繁华夜生活的好;亲戚和同学的陈旧的观念和由于多年生活没有交集而产生的共同语言的匮乏,会让你感到尴尬而你只能用无奈的微笑来化解;和父母每天的零距离接触埋藏了无数矛盾爆发的导火线;一切旧日的人和物除了勾起浓浓的亲切感之外也会勾起深埋多年的陈旧创伤以及随之而来的刺痛感……所以每次在老家住不了多久,就想着回来。老家并不见得有多好,只是他与你人生前十余年的生活重合了,让你感到亲切罢了。你降生到你的故乡其实不是你人生最大的偶然吗?如果生命有轮回,那么你的故乡不就是你人生第一个异乡吗?
每到深夜,我的心愈发可以出离我的灵魂体来审视我自己,我就愈发将故乡视作生命的第一个异乡——在已经走过的人生旅程上,在正在行走的人生旅程上,在未曾走过的人生旅程上,我会拥有一段又一段的乡愁。这些乡愁组合到一起,将会剪辑成你在临死前浮现在眼前的最后一部电影。故乡不是实体,它是一段精神;故乡不是唯一的,它会有很多。然而,当你犯了思乡病的时候,它只能以实体存在,它必须是唯一的。只有怀抱这“唯一”的“实体”,我才能看到我对故乡深沉的爱。
在北方的一座小城市,有我的家;在我的家里,有我;在我的体内,有我的心;在我的心里,有北方的一座小城市;在北方的一座小城市,有我的家。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