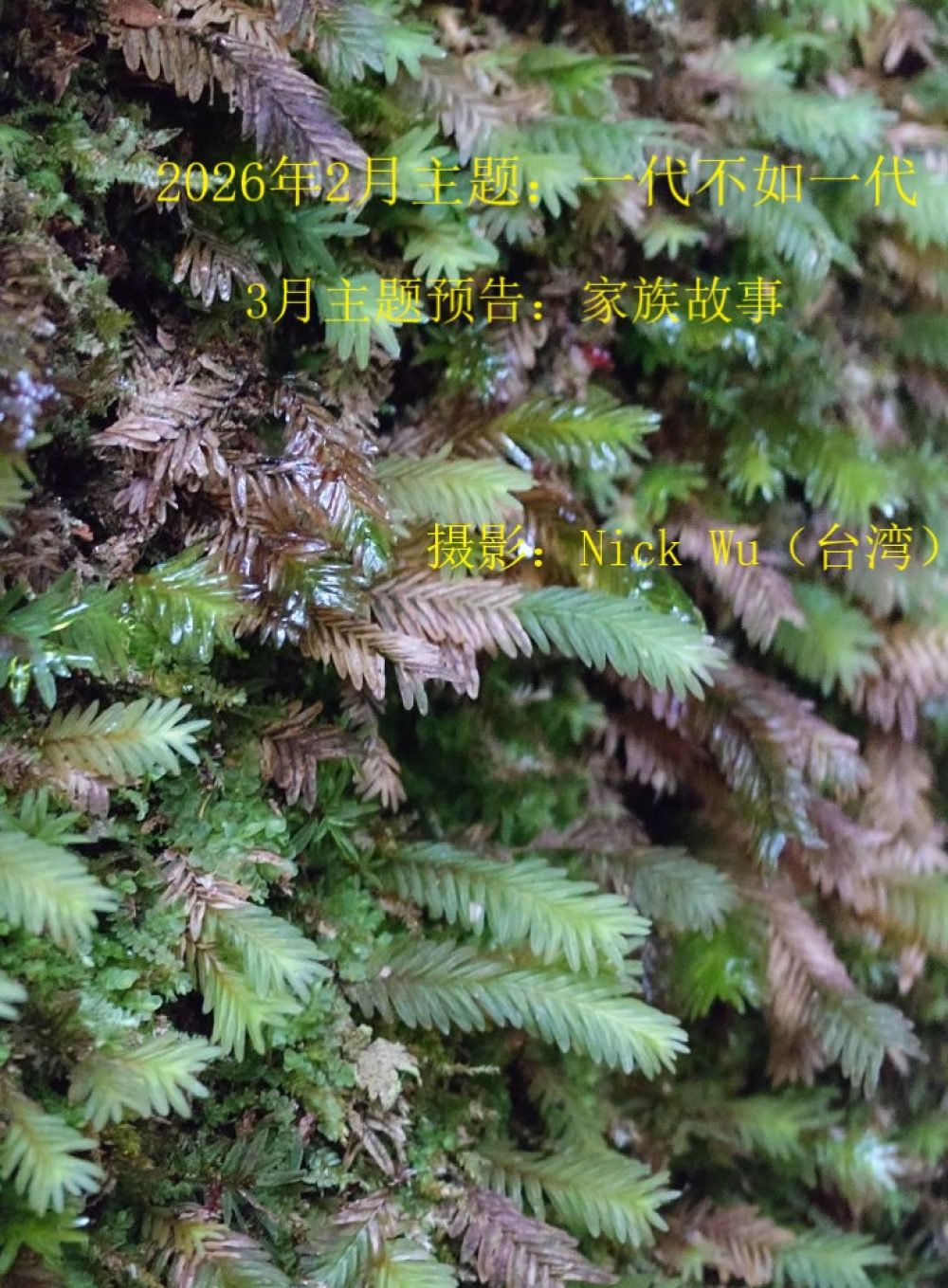遗言我是还没想过,不过葬礼我是很想安排好的。不知算是幸还是不幸,我经历过几次亲友的葬礼,在马来西亚的有:佛教式的、道教式的、基督教式的,在台湾的有:佛教式的,在澳洲的有:基督教式的、佛教式的、巴哈以式的。虽然各有各的特点,但无非就是让死者安息的同时,让亲友们一起回忆一下与死者的记忆,互相安抚一下沉重的悲伤。
不过因为死亡对一般人说来,还是件不容易接受的事。多数人的这些“不能接受”,常会变成怒气,撒在亲友身上是很常见的,对工作人员的发泄也属常事!所以我想,为什么不现在把葬礼好好的安排一下,让我把自己想邀请的人,想说的话,想安葬的方式、地点,甚至葬礼上的摆设,都清楚交代好,这会否免掉那些不开心的摩擦?
人的一生,应该除了婚礼,就该数葬礼是个大事了吧?婚我是结过了,这葬礼我们一般人还是抱着能不提就最好不提的心态。甚至人寿保险,不都还有人当成你在诅咒他短命吗?其实澳洲还是有相当多葬礼公司在卖“葬礼套餐”。我没咨询过,可能还是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总觉得安排自己的葬礼,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毕竟面对死亡,不是去麦当劳买个快餐那么直接、简单。
最近这全球大流行肺炎,搞了快两年了,全球死亡人数多得恐怖,即使不翻报纸、看新闻,也很难不知道。除了大家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人生目标也大有调整。我们一天的二十四小时,该怎么花,事业心该多重,花在孩子身上的心态该如何调整,才对孩子有利而又不会把自己气死,这些调整真是门学问!以前有个朋友她很爱在朋友跟男女朋友吵架后用一个理由来安慰人家,她爱说“如果他(她)明天意外死掉了,你(妳)还会为了这事不开心吗?不会吧?那就好,这根本不算一件事!”我想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假设自己没有了明天,那什么事才能算是件事?我有几个概念希望能留下来。
我个人不想留下太多遗憾。人生嘛,不可能完美,但我希望别遗留太多的悔恨。至于怎么能做到,目前我只能说凡事尽量在做决定之前,收集多些资料(科学的数据、朋友的看法都重要),尽量少些“早知道我就……”的情况发生,毕竟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有了充足的资料,当以后发现没做好正确决定,也只能说情况不一样了,结果当然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还会鼓励大家及时行乐,能帮的就尽量帮,朋友也好,路人甲乙丙丁也罢;在能力范围之内的,就尽量帮。最近我还学会了一招:不能盲目的帮。有时候帮人,也很讲技巧!好比帮街边的乞丐,尽量别给钱,可以问问他们想吃啥,然后帮他们买个外卖,让他们饱腹一餐。因为很多时候这些街友,不太会花钱,而且多数有毒瘾或赌瘾,或有心理病,吃饱比有钱花对他们来说比较有用!帮人,需要用人家真正需要的方法,而不是自己认为对的方法。
我想我还会做个PPT,把我从小到大、到老(如果我可以再活个二三十年的话)的照片整理一下,让亲戚朋友能回顾一下。然后这PPT还必须放上我的脸书,让大家想我时候可以看看我,就有点像酒瘾发作时候闻闻酒香来顶一顶瘾的味道。当然还得加上我的一段话,让我的声音也有机会留在人间。毕竟人的记忆是信不过的,有照片、声音的记录,比较可靠。脸书会一直在网上吗?可能还是得放上云端,不然只剩下墓碑上的一张照片,也太少了吧!我记得有一次去扫墓,我妈说:“看,人嘛,最多留在世上的影响就只有三代,过了三代,连墓碑在哪,都不一定有人知道。”凭良心说,有几个人对自家曾祖父有概念?父姓是知道的,但是曾祖父的名字大概就要去翻族谱才知道了。至于有什么人生格言,人生经验留下,恐怕就更谈不上了吧?除非是个伟人,不然连名字都留不下来,套我那女朋友说的,这样的人生不算件事!
其他的,对我而言,其实都是不太重要了。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脚一蹬,眼一闭,就是尘归尘,土归土。棺木的材质设计、葬礼的形式排场,甚至下葬的方式,我觉得都该越简单越好,所谓的走个过场就可以了。这些在我眼里,是为了死者家属置办的。我觉得把钱省下捐给慈善组织比较实际点。其实我也很赞成把身体捐给医学院让学生来做研究、学习。有点废物利用的概念。比变成肥料被植物吸收了要好吧?不过我认为这还是应该留给我儿子决定,他能接受的是土葬、火葬我都无所谓。如果我老公死在我前面,那就我儿子用最便宜的方式解决我的葬礼;要是我死在我老公前面,那就让他决定一切,我知道他不能接受火葬、捐躯给医学院等的想法,那就罢了,反正我的概念就是哪个方法让家属舒服就用那个方法。我想现在是时候跟我老公谈谈这话题了,免得万一突然得面对,就成了件太头疼的事了!
上一篇文章链接:沿途风光明媚/#练鱼(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