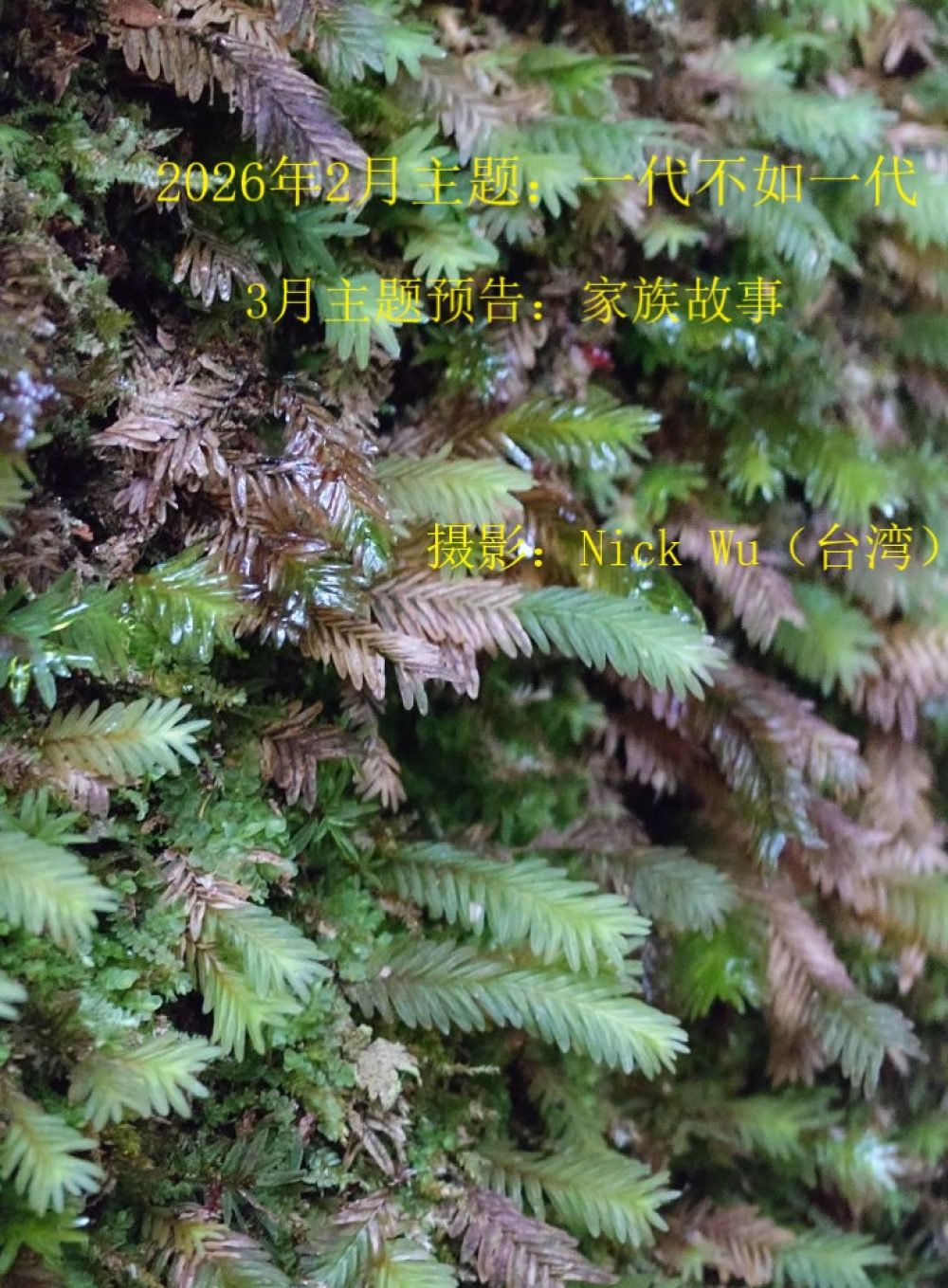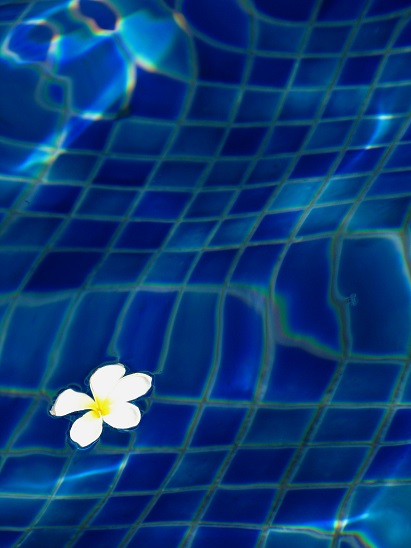对于记忆力好的人来说,不忘记就只是单纯的不忘记,和念念不忘没丝毫关系。这种特质自然有好处也有坏处。背书的时候想当然会比较占便宜,但脑袋里垃圾装太多偏又倒不掉,那就实在没什么值得可喜可贺了。如果真能够过目不忘倒也不错,可惜通常又还不至于,或许是缺乏训练,右脑尚未开发,也可能脑袋天生只适合装些鸡零狗碎。
人家吃了龙肉才开始感觉有点值得回味,你对七年前那一顿平淡无奇的粗茶淡饭却好像才刚放下筷子,齿颊不留香,记忆不褪色。西方有一个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的说法,“眼不见,心不念”的翻译彻底掩饰了死没良心的本质,说穿了也就是一种类型而已,无谓苛责。记忆力好就不需要经历过倾城之恋那种大场面才对故人念念不忘,认识已经注定不忘,虽然不忘和念念不忘其实还有距离,很远的距离。所谓不忘,就是平时把往事尘封在记忆的某一个角落,不见得常常叨念,但那个角落绝对伸手可及,好事也好,坏事也罢,要翻随时可以翻出来。
即使记忆卡容量够大,还是难免怀疑老天爷到底有什么特别用意吗?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可是不忘那些看不出意义的人与事真的很无聊。鸡零狗碎等“准废物”除了丢进垃圾桶,现在还流行一个当堆肥的新出路。这就有点随时准备发挥作用的意味了,不过似乎还是高兴不起来,有机肥不就是鸡屎的同类嘛?
把鸡屎放进脑袋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个人选择,天生如此,徒呼奈何!唯一比较可行的对策,就是不把事情放在心上。脑袋记得是记得的,但是心里不当一回事,就算明镜有台,大概也不会太招惹尘埃。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倒说出来听听。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