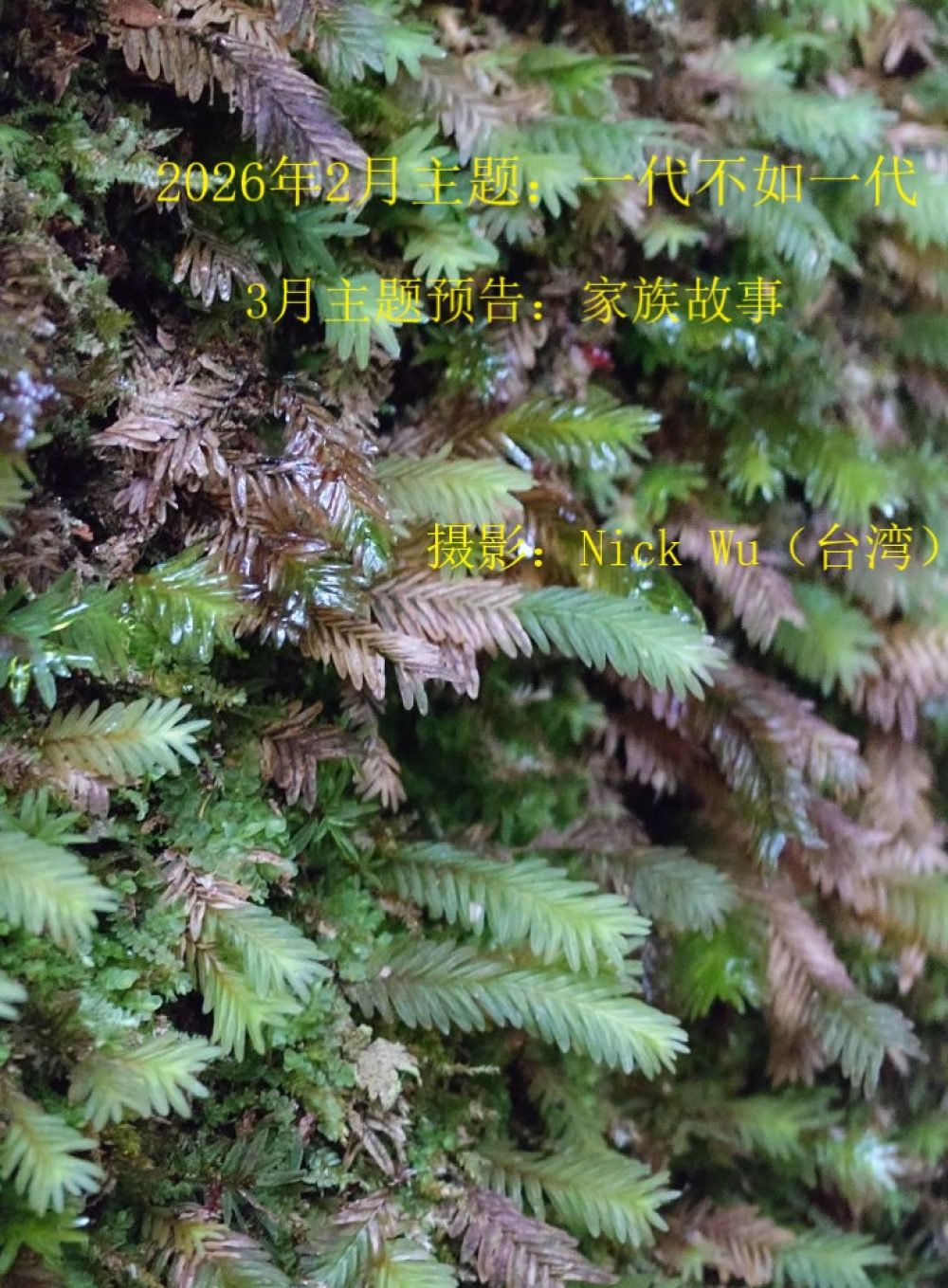刚上车,后座的小瓜就抛出这样的一道问题。这问题可大可小,必须谨慎应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嗯。”为了争取时间思考,假装很忙,换挡退车,再换挡让车子从幼儿园缓缓开出,然后回道:“我想应该是会有一点孤独吧?”四平八稳的先回一句,从望后镜看着她那乌溜溜的小黑眼珠问,“为什么问这问题呀?”
“我没有朋友。”说完,泪珠在眼眶里滚来滚去,没差点掉下来。看了心都碎了。
“玛丽呢?她不是妳的好朋友吗?还有‘克雷蒙’和‘阿肯’,他俩午休时常和你一起吃东西,不是吗?”脑袋拼命的在搜索她曾经提过的名字,再提出一些不慍不火的反问句。目的是让她记得她还有朋友,也希望从这些名字中,得知她最近的交友状况。
交朋友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童年时,只要能够一起玩耍的就是朋友,虽然都叫不出彼此名字,可是仍然可以打打闹闹的玩在一块。那时的友情很纯真,都是用颗真挚的心去和朋友分享东西,从不勾心斗角。
同学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拿了舅舅的一套金庸小说借我,被发现后,他舅把他揍了个满头包。隔天上课,他指着头上的淤青,告诉我缘由,看着他的头,青一块红一块的,我们哈哈大笑,放学后照旧去玩抛拖鞋比赛去也。也没有因为被揍而对他有任何怜悯之心,照样把他杀个片甲不留。
当时的心里,没有一丝丝的内疚和不好意思;不是因为脸皮厚,而是觉得,如果情况相同,我也会做一样的事情,那是理所当然的。
小学毕业,各自上不同的中学,尔后不曾再见。若干年后的同学聚会,远远的看到并喊了他的名字,握个手,说声:“嘿!”相视一笑,童年往事竟如海涛般涌上心头。虽然错过了他的婚礼,也没有来得及参加他女儿的弥月之喜,他舅因故离世时我更加不在场。闲话家常中,把彼此在岁月留空的部分,一点一点的补上。
那天的聚会,仿佛行走在月球上,轻轻的没有大气压力,内心却实实满满的、很是欢悦。
“那是‘玛格丽特’啦,爹地!你把人家的名字都记错啦!”小瓜破涕为笑,“玛格丽特说她只是和我一起玩,没有答应跟我做朋友。”“哦,那,那个阿雷蒙和阿肯呢?”我问。“克雷蒙和阿肯说我们只是一起吃饭,不是朋友;他们说如果男生和女生做了朋友,最后是要结婚的。”
现在的小朋友。
把车子靠左放慢,指着右前方的一棵树道,“看到那棵大树吗?” “哪一棵?”“喏,右边那棵,树顶长满小黄花的那棵。”“喔!漂亮的树。”“你觉得它会有朋友吗?”
小瓜喜欢老爸给她问问题,马上目不转睛的盯着那棵树,大树随着距离逐远而变小,然后消失在转角处。
小瓜这才回过头来说,“没有㖿!”一双小胖手一摊,“我不知道它的朋友要怎样来找它玩?其它的树都离它很远,没有要和它做朋友的样子。所以它是棵没有朋友的树!”小瓜自问自答,然后给出结论。
把车子徐徐回转,在离大树不远处靠左停下。
“其实,大树有很多朋友。”我认真的说。小瓜听了,把她那乌黑眼珠张的大大的、充满问号的望着她爸。“风儿就是大树的朋友呀!妳看它们谈天谈得多开心。大树笑得把叶子也抖落了一地。”
“只有一个朋友?” “当然不止一个啦。大树的朋友还有小鸟。每天清晨,小鸟就会飞过来,唱歌给大树和它周遭的朋友听。”
“还有,松鼠也是大树的朋友呢。”“哈!那怎么可能?松鼠又不会唱歌。”小瓜抗议。我说,“松鼠常常拿一些果实来问大树是不是它掉的。”“然后?”“如果不是的话,松鼠就把果实吃掉。如果是的话,松鼠就会把果实留在树上。”小瓜听了哈哈大笑,“我才不要我的朋友把东西塞在我的头上!”
“不要忘了,小雨也是大树的朋友哦,它偶尔会来找大树讲话。可是每次小雨讲的东西都很悲哀,大树听了很伤心,哭得稀里哗啦的。”
“哈哈哈哈,爹地你骗人!” 从望后镜看到小瓜眼神,见她满眼笑意,知道她已经暂时忘了朋友和玛格丽特的事了。
天气开始转凉了,开车继续上路。到家时,小瓜已经睡倒在后座。抱她上床,让她和衣卧下。窗外,风儿和小雨来看她,告诉它们她已睡了。离开时,轻轻把窗掩上。
雨也停了。
摄影:李嘉永(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