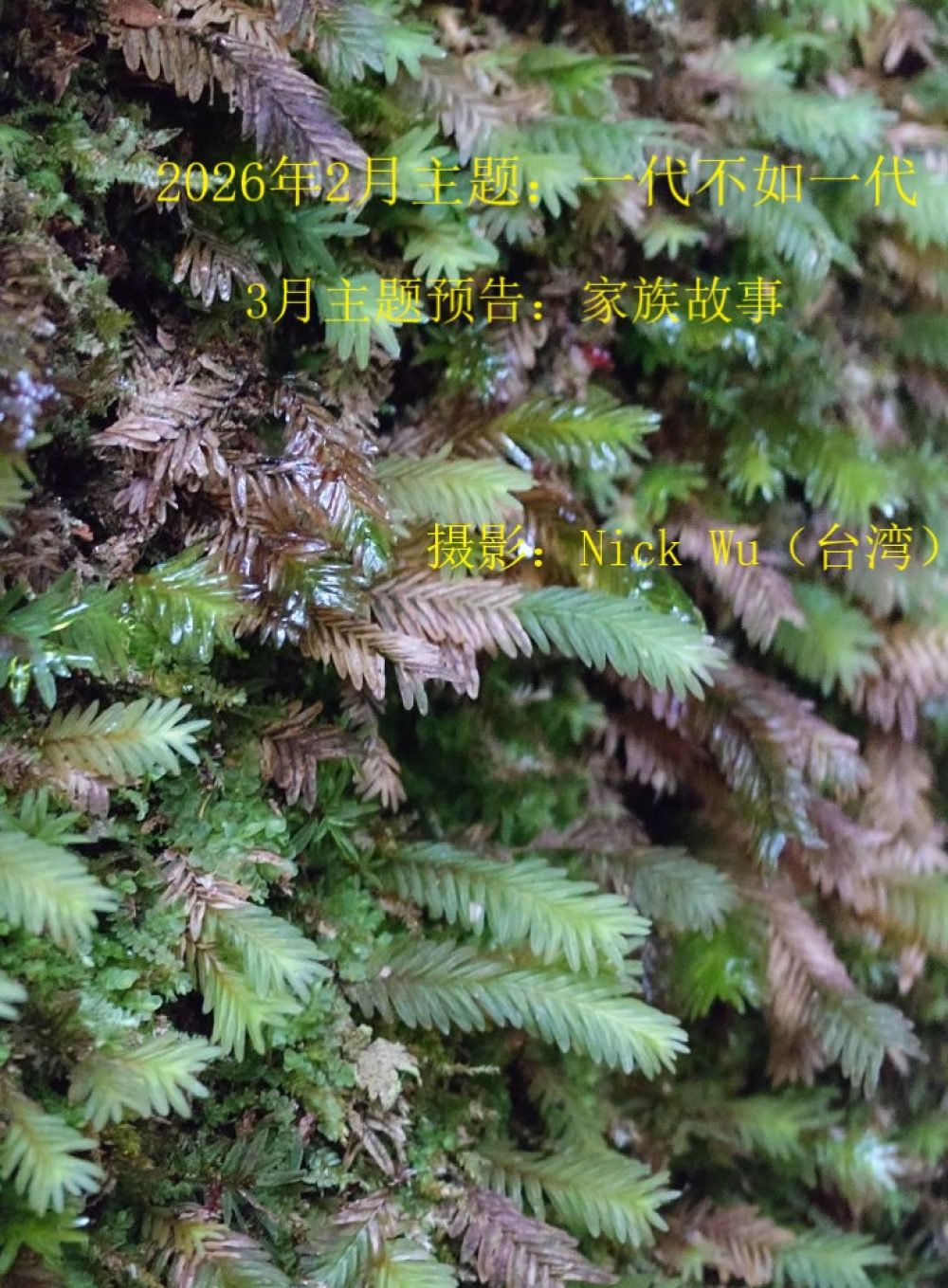在研读德文十九世纪经典哲学文本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时难免会进入一种错乱的状态里。在那个紊乱的概念世界里,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甚至有时会怀疑究竟那些所谓的人文科学,是否与伪科学能作同等处理。也许,在那一派称作“分析哲学”的概念里,就会用这个来否定多元的百花齐放,非要切割到组成物质精神的根本单子(https://goo.gl/9gBJQc)不可。
要求清楚明白固然是科学精神可以重复验证的根本,在物质世界里,似乎相当可行。所谓的科学试验,不就是如此进行的吗?但是,能够按照物质的排列来解释精神世界的所有可能吗?甚至,按照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物质世界的位置难道就犹如测量工具那般局限下确实的清楚明白吗?
以上两段话,仿佛痴人说梦,莫非就是苦心经营欧陆哲学之下陷入的窘状?认真读过这有名晦涩难懂的文本者,也许不需要在仿佛绝境的绝对精神下放弃理解的可能。但是,也不必在心情郁闷时勉强囫囵。此时与其为难自己,不如转向伟大的中华文化来用自我中心来揣测,用分析综合的二分以外的语境来诗化?
诗,三百,一言蔽之:思无邪。
于是,伐木丁丁。
“丁”,要用什么音来发呢?
这就来到如题。《集韵》:“变”古作“𢒪”。
几个月前偶然看到几年前发在网络的一篇旧文有人评价:逼格有点高。逼是我在一位浙大教授说明下理解其根本含义的。这篇,不就更加装牛逼吗?
也许,是人如其文吧。突然的就岔开跳到不知所云的境域,也不求知音也不关对牛弹琴,就权充学会一个异体字,日后能用来唬人,显摆。
确实是时代改变了,以前读到汉高祖问问自己的姓氏含义,查什么字典也就得到姓氏两个字。现在把它放到异体字的网页去看:折杀奴家也!(编按:可参考以下网址https://goo.gl/WIHwii)
摄影:Nick Wu(台湾)
注:我用自己的理解来诠释一下内容:“𢒪”是“变”的古代写法,怕了吧?(周嘉惠)
注2:发现不是每一架电脑都能够显示这个异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