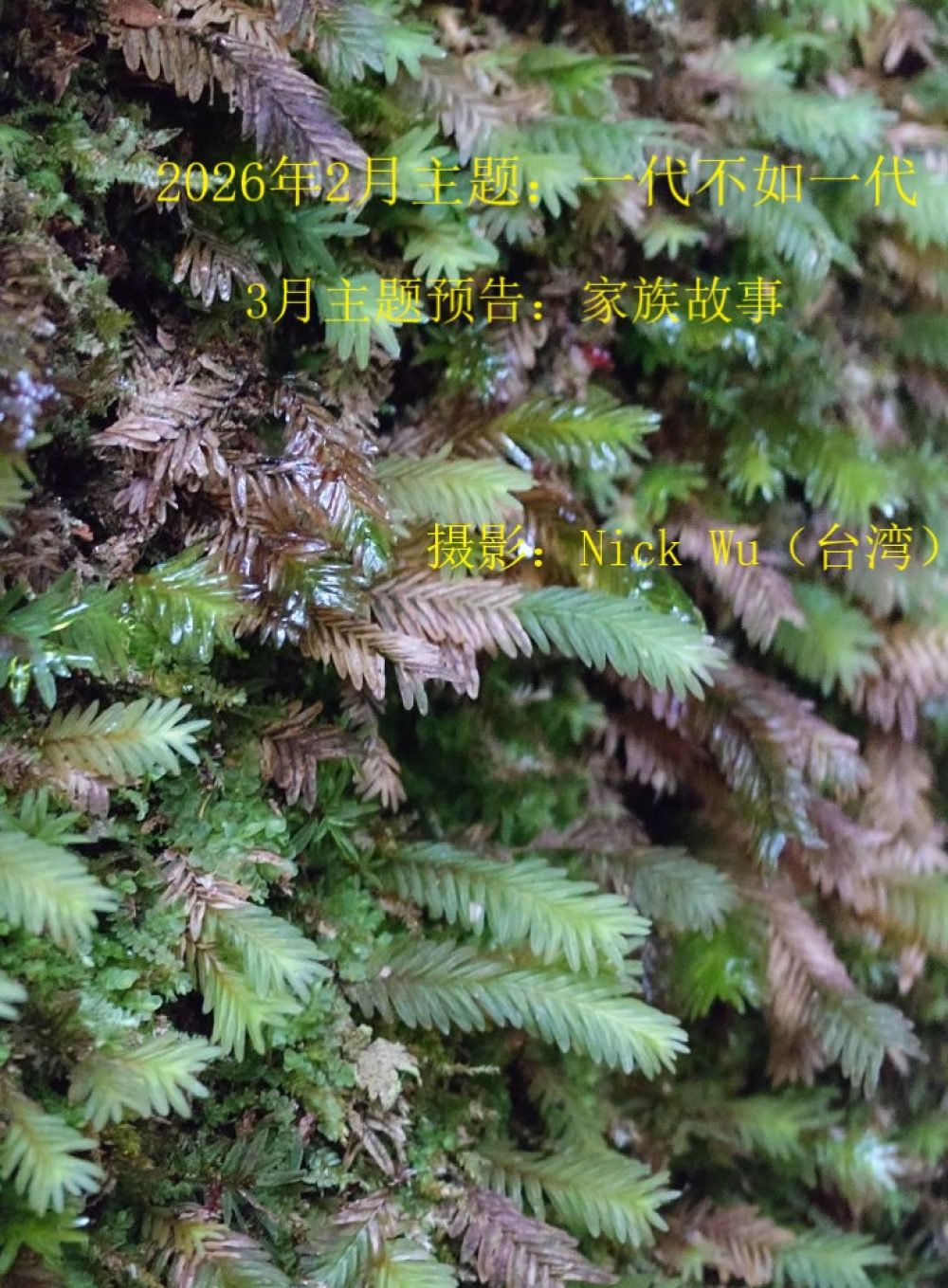有个大学副校长嘀咕着科学院如何的用钱。“这些搞科学的,购买研究器材动辄就用去数百万。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数学系,只需要铅笔、纸和一个大废纸篓。哲学系更妙;他们只需要铅笔和纸。"
取笑哲学家或学哲学的人是很容易的。以泰勒斯(Thales)为例:他是古希腊世界第一个信誉好的哲学家,生活在约公元前七世纪。有一天,在走路时看天上的星星而掉落井里,把附近一个美丽的婢女逗乐了。
从那时起,因看星星而掉入脚下的各种陷阱就成了哲学家们的命运,引来看客们的冷嘲热讽也惹笑了他们。
哲学家的笑话一箩筐。笛卡儿(Rene Decartes)在他喜爱的酒吧喝酒。近打烊时,侍者问他还要不要再来一杯。他回答:"我不想--"顷刻间他如烟消逝。
这是个内行的笑话。要笑得出就必须知道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他超过任何重组希望地把身体和心灵二分。
哲学学生倾向于如笛卡儿式"我思故我在"的傲慢精英主义。以此推论,大多数人不像哲学家般思想,所以他们实际上不存在。怪不得人们喜欢取笑哲学家。
几年前我告诉古晋一家我喜欢去的咖啡店老板,说我会到吉隆坡一家私立学院教哲学。他露出不解的表情带点不好意思地问我:"哲学是用来干嘛的?""比如说用来开咖啡店,"我连眼皮也没动地回答。我的捉狭引来哄堂大笑。
我在教书行业的历程证实了是短命的。除了班上一成左右的顶尖学生,大多数在容易取分上比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存有学及形而上学、或是康德建立先验综合知识的尝试,来得更有兴趣。一两个怪僻的同学可能会对存在主义好奇,我们就略略地讨论自杀的议题。
这场景使我想起德里达(Jacque Derrida),著名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法国哲学家。(当然必定是长长的"XX主义",他在几个月前自我解构,与世长辞了。)
德里达像之前的许多伟大哲人一样,常在未被阅读或理解之下被引用。对那些还未曾被启发的人,他的作品是很难明白的。试读下列的几句:
"有人,或你或我,前来说:'我要终于学习生活了。'终于,为什么?学习生活;一个怪词儿。谁要学习?教导生活,向谁呢?咱们会有一天学习到如何生活,最主要的,'学习生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终于'?"
"它本身,意境外的--却又是个意境,是常开放的,也因而会错及不足--那个词儿几乎形成一个不可理喻的字义(Syntagm)。它的成语能到什么程度如何去翻译呢?"
谜样的问题;即使大多数人都有时候会对生命和生活有所困惑。但是德里达的道说是那么的不透明,只要在他那一两页不可理解的东西挣扎后,一般马来西亚读者都会把书搁置。那些真的对哲学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在非常激动下把书向墙壁砸去。
所以,大多数人都离哲学远远的。反正你可以在不知道任何哲学寯语下很好地过活。事实上,不少业余沉溺在哲学的少数人会变得更加不成型、更加混乱。
在任何情况下,在那些罕有的生命意义变得不安的时刻,总会有辅导员、精神医师、激励讲师、甚或是算命师在一旁候命。当人混乱时,他需要确切的答案。哲学--如以上德里达说的--要比答案产生更多问题。
但我在一个理由上记住了德里达。他是个专业哲人;一生人写哲学文章教哲学。而他也是在一个悠久的法兰西传统,也许是从艾密里.左拉(Emile Zola)开始的,对待哲人如对待一个从远处观望政治权力中心的积极参与政事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其中一个成就是成功推动和组织法国的家长延续高中哲学的教导!
咱们很难想象在中学教导哲学。但是在法国,哲学一直是中学课程的一部分。当那个地位动摇时,德里达和他的友人成功酝酿出足够的压力来重述教导这看来无用的科目的需要。
这种事不会在马来西亚发生。事实上,如我所知道的,在马来西亚众多高等院校、大学,并无一有哲学系,虽然有一些入门课程。
如果我成为教育部长,我会命令马来西亚每一大学成立完整的哲学系,而且哲学101是所有学士课程的必修课,包括发型设计和插花艺术。
幸好对家长和学生而言,马来西亚曾进修过学术哲学的人少过一个手掌的指头。那种科目是弱势的,所以我的命题会过早无疾而终。
再说,我也不大可能成为马来西亚的教育部长,因为在没有经过我同意之下我被列为华人。在马来西亚,没有明文的法则说做内阁部长是比任何神圣宪法上的法律平等上是更有权力的。所以,你不必担心你的孩子们会把厚厚的哲学书向墙壁砸去。
我最好还是不去回答诸如"哲学是为了什么?"或"哲学是什么?"的问题。苏格拉底在公元前五世纪尝试过了。雅典的城邦人民用民主的方式以"误导青年和祭假神"的罪名判他死刑。被误解嘲笑总比被令饮鸠好。
我可以想象苏格拉底在今天的吉隆坡。看看他,试着在富都巴刹或金河广场招徕群众,口里说着不曾检验的生活不值得一活等等。
有些马来人大概会恫言用石头来扔他亵渎伊斯兰教。有些华人会看在他破烂的衣服上让一个铺位给他。有些印度人大概会在任何事和他争执不休。警察或市政局执法人员大概会问他要咖啡钱,或者以他没有任何准证拘捕他。老牛邙不能在"能国"呆上一天。
我曾读过一位马来西亚女作家写过对哲学和哲学家的好奇。她的结论是修辞地"为什么要阅读死去的白种男人写的书?"
的确,为什么!只要咱们有大量的修辞式问题,咱们可爱的一句式话语,咱们晚间重述政治老大不言自明的真理说的超越教堂的新闻发言人,咱们伪装的传统亚洲智慧,为什么要咱们追求真、善、美这些鬼东西?
再说,真善美有什么用?
哲学吗,哪位?
(摄影:Cl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