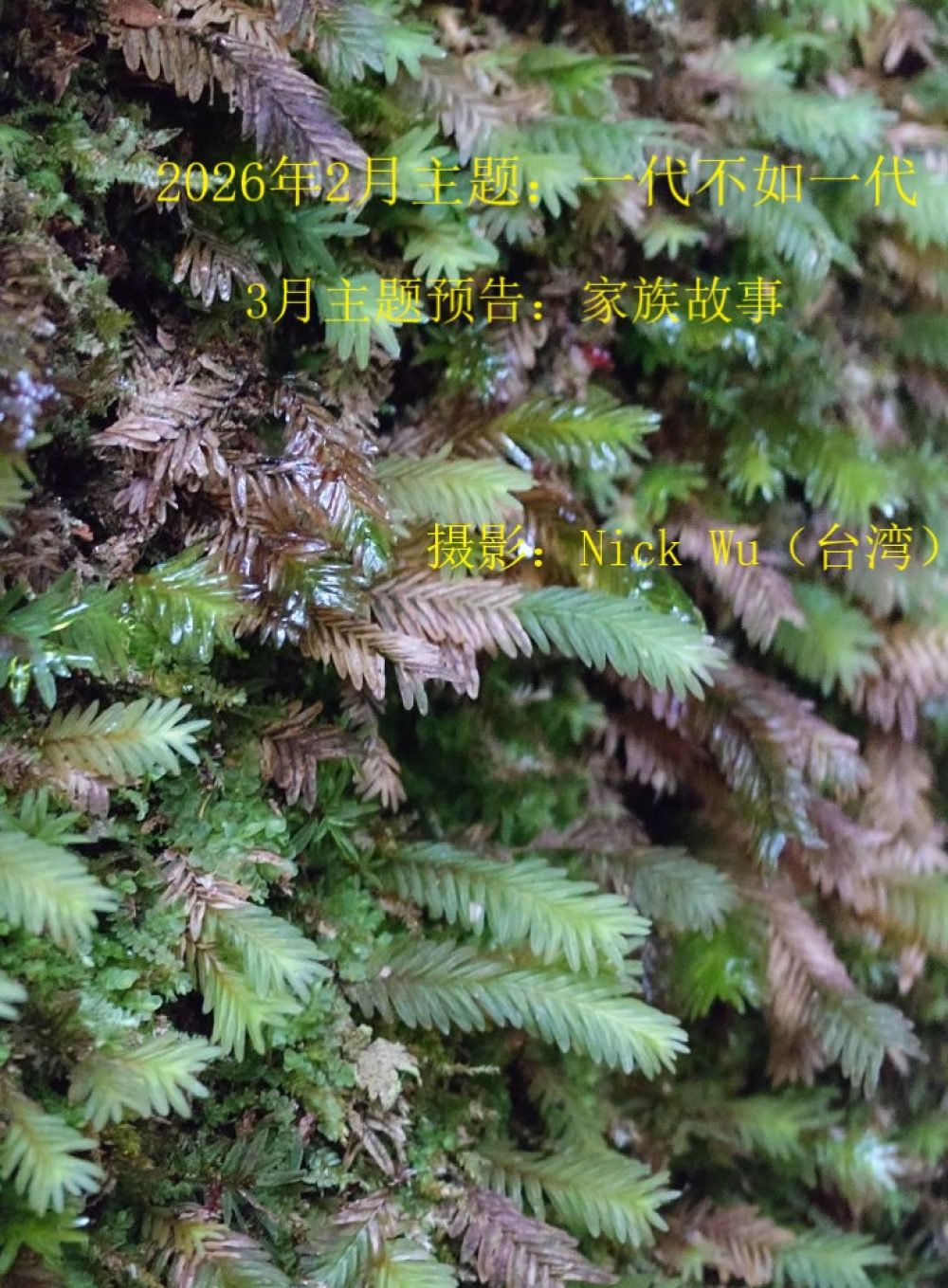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人文”这个概念现在四处可见,且成了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它既可以是学院派与当权者树立对芸芸众生的关怀姿态的修辞,成为权力机构纹饰宣传的点缀;又可以是普通民众借以标榜自己文化修养的符号,甚至沦为商品推销的手段。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文”?笔者试图通过对西方人文主义观念之源头的考察,从“复古”、“抵抗”与“理解”三个方面,谈谈自己对“人文”观念的一些粗浅认识。
首先,是人文主义“复古”的一面。“人文”的概念在思想史上正式提出完全是欧洲文化的产物,严格说来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倾向对抗保守禁锢的基督教经院哲学的产物。在1392年的2月1日,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的学生柯卢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给友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视作是人文主义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信中说道,不是驽钝死板的经院哲学、而是历史,活生生的历史,才是人的教育者和塑造者。那些人在世界上交往与行动的鲜活记录才是关乎人性的最宝贵的“知识”。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回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原典的根本目的所在。对“古”的复兴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人性”的探究与张扬——不要忘记柏拉图的所有文字皆无一丁点第一人称的理论表达,而全都是“记载”苏格拉底及其友人们的交往言行的历史剧本!所以可以说,人文主义对古希腊哲学的高调回归,不是“哲学”的,而是“文艺”的。经院哲学已将形式逻辑的诚实可靠发展到了一个巅峰,但人们发现对原典越来越繁复的形式逻辑解释,反而与“人”、与“自我”越来越远,所以人文主义者的口号是越过形式逻辑的重重障碍,用个体的、审美的方式去直接感受古代原典中的每一句话。所以从词源学意义上讲,“人文”不仅不排斥文化民主化,反而它正是民主的甚至民粹的。人文“复古”所反对的恰恰是知识独裁,人文概念天生就带有强烈的山野性。
其次,便自然来到了人文“抵抗”的一面。正如上文所述,人文主义者是带着一种对经院哲学束缚性的强烈的抵抗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与当今我们通常理解的人文乃是抵抗商品经济社会的物质化是截然相反的——恰恰是这些物质化的商品经济参与者,推动了人文主义的发展。他们资助了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创作,鼓励美术家在画作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在中世纪的圣像画传统中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正是在这种商品经济思潮下,文艺作品也可以成为商品的观念才首次进入创作者的头脑中。商品经济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丰富的感官享受,带来了尘世生活的无比快乐,这正是人文主义者歌颂的东西!这里尤其要提到文艺复兴时人文主义作家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言论:在一篇对话中,他说渴望金钱不仅是人的自然本性,而且还有益于文明社会;在一封信中他更是直截了当的说“金钱是国家的力量所在,赚钱应视为国家的基础和根本。”不知读者有否明白人文主义者真正抵抗的是什么?的确,从表面上看,是虚伪的宗教禁欲主义;但从根本上说,正是世间的一切“虚伪”的“主流”本身。社会主流压抑性欲,惊世骇俗的《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出来了;政治主流崇尚道德,宣扬权术的《君主论》出来了;生活主流只谈圣洁,以《巨人传》为代表的屎尿屁文学出来了。一旦权力形成实体,为避免个人主义对实体的分散力,必然要以一种道德体系来维系权力实体的存活:当今种种近乎疯狂地强调凝聚力与向心力的企业文化、拓展培训之类正是这种东西。而人文主义所抵抗的也正是这种东西。
第三,如果说人文主义者在诞生之日便肩负了对主流道德体系的“抵抗”使命,那么“抵抗”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吗?笔者认为不然。“抵抗”是方式上的硬性,是对禁欲主义的现实的一种发难,而其软性的目的乃是“理解”:对“人”即人的肉体与精神世界的全面理解。对“人”的全面理解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的核心。彼特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我只想要凡人的幸福。如果我只对飞禽走兽的特性知道的很多,而对人的本性一无所知,那又有什么好处呢?”通过全面理解人,进而全面开发人在心理与生理上追求快乐的一切潜能,更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菲莱尔福(Francesco Filelfo)说:“人们怎么可以忘记人的身体呢?我们既然是大自然的产儿,就应当竭尽全力保持我们肢体的健美和完好,使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免遭来自任何方面的伤害。”理解了人性中很多负面的东西,便看透了一切正面宣传的脆弱性;理解了人的自然性,便理解了人的野兽般的欲望,甚至对此进行歌颂——直面欲望而非对欲望进行文化上的转移和加工,这才是人文主义的精髓所在。为了对情欲进行深入探究,达·芬奇甚至精细地描绘过性交过程中的人体解剖图,这就是不顾一切的“理解”!故而这种“理解”与其说是一种科学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姿态”:顶天立地的“我”在此,无所顾忌地追求我所认为快乐的事情,这就是人文主义。它只和“我”有关,而与“我”之外的所有文化符号层面上的升华全都无关。
反观今日人文主义的境遇,笔者认为,从人文观念的上述起源来讲,今日的人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其初衷,从生机勃勃的突进力量凝滞成了一股僵死的、老朽的思维和说辞。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乃是尖锐的冲突。老祖宗的“人文”不是退守,而是在时刻存在的危机感下,激起身心的全部敏锐感知力,张扬人格,锐意进取;而今日,学院派代之以越来越繁复的文化符号和理论概念,山野派代之以空洞乏味的修辞点缀,这难道不都是对人文精神的背叛吗?回到起点,今日强调“人文”,不是强调理论修养,也不是强调文化修辞,就该是强调个体对外在压迫与内在欲望的感知力而已——通过提高这种感知力,明白“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才是最根本的人文关怀。莫将之符号化、复杂化,就这么简单。至于这感知力所导致的行动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那就是伦理而非人文的探讨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