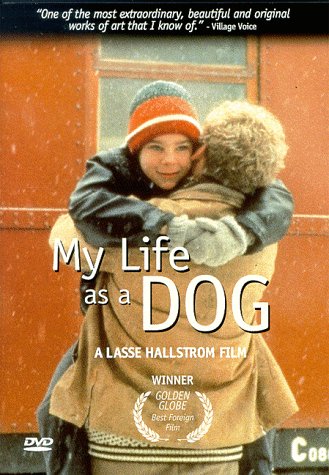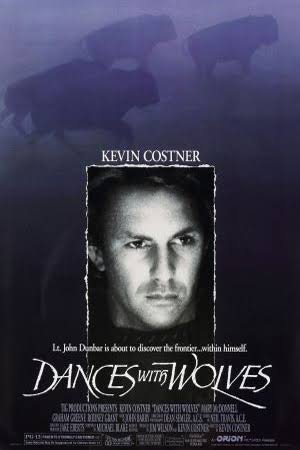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留下一句特别让人玩味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能够是因为河水变了,人也变了。
如果不是存心抬杠的话,我们对赫拉克利特“万物流变”的思想有点感觉就够了,不必和古人较真。河水变了,感觉上还没什么,但是这一分钟的人和后一分钟的人确实已经经历了一点点的变化,那却是让人思及不免惆怅、失落。
这句话也让我联想到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里开始的那几句歌词:“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谜总是看不清,其实我用不在乎掩藏真心。”在还没接触古希腊之前,觉得云、梦、谜已经足以表达变化多端的意思了,而且带有一丝朦胧的美。至于人家懂不懂我的心,坦白说我可是从小到大不曾在乎过,自己懂就好了,别人不懂我损失什么?
这种性格在年纪大了以后也无所谓了,年轻时代就比较麻烦,三不五时会有女性朋友气冲冲地喊:“你根本不懂我!”我为人向来比较小心,总是试探地问:“恭喜?”然后,也就没有什么然后了。回想起来,难说损失的究竟是我还是对方?人一直都在变,试图去完全理解一个正在改变的人,除了傻,也不可能办到。多年后认识了赫拉克利特,觉得“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实在是深得我心,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前世是不是赫拉克利特?其实,我玩的正是这一味,至于别人都在玩味什么就不清楚了。
在马来西亚,城市地区大概已经找不到还没有被污染的河流了吧?那些臭水河,谁会想去踏入呢?别说两次了,一次也不想。至于郊区,或者人烟稀少的森林地带,河水是相对清澈的,可以见到河水中的游鱼,如果更仔细地看,“幸运”的话甚至可以看到蚂蝗(水蛭)!总而言之,反正我不想踏入马来西亚任何一条河流。
话说回头,虽然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我一直认为,人应该都有第一次踏入河流的冲动。自古至今,人心不变,我们都有试探水温、水流速度的好奇心,而不大胆第一次踏入河流,我认为只是理智压倒人心的结果。
人的流变,就像手中逐渐流失的细沙般无法真正完全把握,得而复失怎不让人惆怅?而人心不变,却让我们有机会和古人平起平坐交朋友。阅读就制造了这一种契机,偶尔,我仿佛在书页中感受到赫拉克利特等古人的会心一笑。
那一刻,感觉就是很好。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