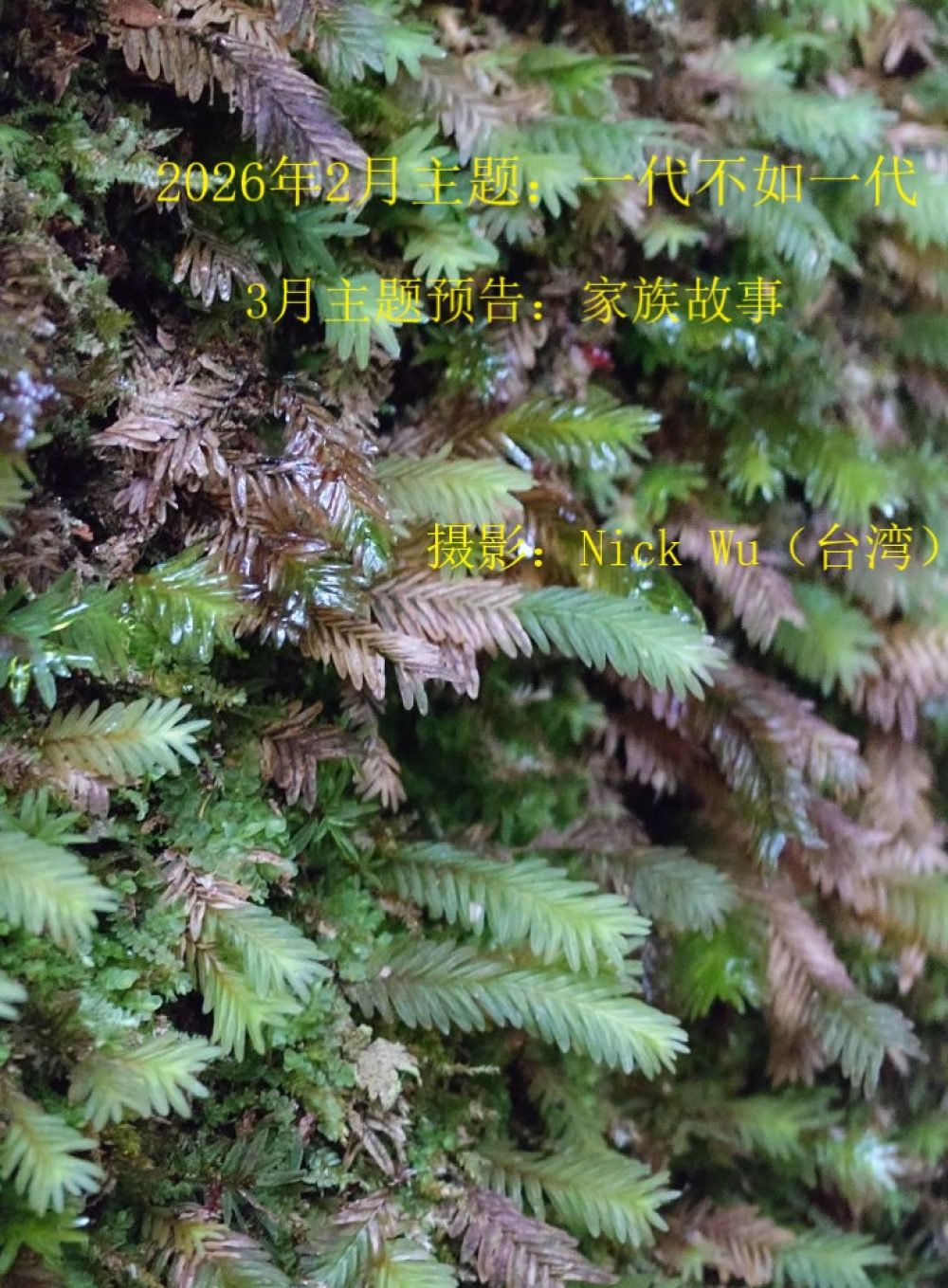2020年刚开始的这两个月,马来西亚正承受着两种病毒的夹击:1)A型流感,2)新型冠状病毒。前者已经施虐有一段时间了,情况比较严重。后者突然从天而降,虽然国际卫生组织一再发出警告,但至今为止,至少在马来西亚国内情况来说还不算太坏。
两种病毒简单来说都属于感冒类,应对的方法基本一致,无非就是勤洗手、戴口罩、量体温、隔离。或许媒体二十四小时的轰炸成功营造了恐怖气氛,以致口罩、洗手液近来卖到断市。网上甚至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笑话:以前是戴着口罩抢钱,现在是带着钱抢口罩。据知有些学校、补习班、安亲班最近开始规定学生必须戴口罩以策安全,但是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路人戴口罩的顶多占百分之十。这是不是意味着口罩抢归抢,戴归戴?真不知道抢购口罩究竟是为了预防病毒,还是纯粹抢好玩?
新马两国的人都一样的“怕死”(kiasi)又“怕输”(kiasu),谁也不必谦虚。不过抢购口罩的全民运动看来比较像是出于怕输心理,否则好不容易抢来的口罩应该都戴起来才对,不是吗?
现在许多场合也开始了测体温的措施。一旦被测出正在发烧,学校会要求家长把孩子带回家,其他机构也会阻止患者进入大门。预防胜于治疗是正确的策略,但前提还是需要有常识。怎么说呢?譬如人的正常体温是摄氏37度,这一点必须搞清楚测体温才有意义,虽然仅仅知道这一点也不见得就足够了。最近有次在某机构入口处接受测体温,33℃,没发烧,请进!估计这门卫应该不是丧尸电影、电视剧的粉丝,否则33℃的体温真的很应该怀疑我是丧尸才对啊!
如果不具备基本常识,我们其实是不需要进行测体温这种科学行为的,去庙里求神就行了。全能的神明如果能够保佑我们中万字,当然也可以保佑我们对抗病毒!
提到求神,想起朋友传来的一段网上对话截屏。有位住新加坡的中国人十分不满意当地政府不停课、停工,认为简直就是佛性接受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其实,不论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都好,病毒不是不存在,但我们还有紫外线呀!虽然连专家都还没完全明白新品种病毒的路数,但似乎这种病毒并不那么适应赤道的温度呢!否则新加坡哪还有这么多人精力旺盛地去抢购卫生纸?
放心吧!菩萨、上帝、阿拉会联手保佑我们的。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