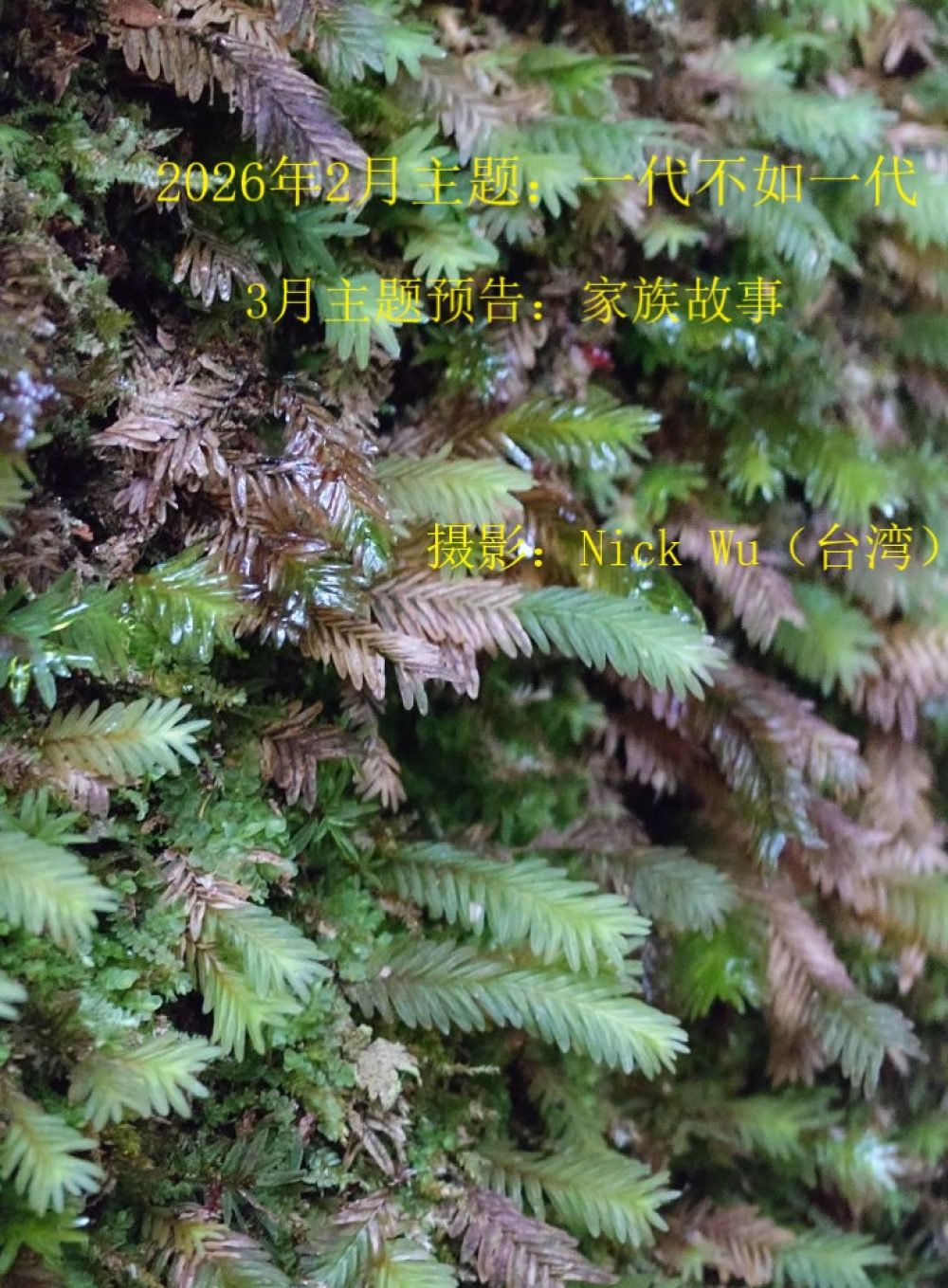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约翰福音1:1)(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注)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表达是生命存在的证据。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表达意味着生命,那么的确,谁的声音大谁就有道理。一群中老年妇女在小区的广场上跳舞,伴奏是极吵、极单调的摇滚乐,叮叮当当,大刀阔斧,释放着与她们的年龄、体态不相称的力比多。音乐的魔力据说可以大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每个广场舞者的胸腔中都有一颗衰老的心脏,它像一台年久失修的钢琴,偏离了生命的音准,奏不出美妙的旋律。只有除颤仪和单调的、广场摇滚乐的打击能勉强帮助他们找回生命的节奏。摇滚乐的节奏据说就是性交的节奏。心脏按摩就像自慰,音响必须开到最大才能穿透灵魂、到达G点。用大喇叭强行改变别人的心跳节奏,这是广场舞难以推诿的罪。一个想午睡的人,一个下班后极度疲惫的人,窗外传来的广场舞音乐,会强迫他的心脏进入性交的状态,感觉就像睡梦中被强奸,而死神在一边观看。广场舞者是蚊子,是淫魔,是吸血鬼。他们的生命是偷别人的,他们的脸上带着贼的笑容。他们乐此不疲,所以他们才能延年益寿。但至少在小区里,她们能够维持这个特权,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她们的亲骨肉。但她们应该意识到,亲骨肉更不该乱伦。据说就有个年轻人发明了定向喇叭,相当于给乱伦者戴上了安全套。
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但权利是一个悖论。生命权之所以是毋庸置疑的第一权利,是因为只有幸存者才享有生命权。每个人都在这个时代想尽办法表达自己,而选择总是越来越少,越来越极端。年轻人会进歌厅、酒吧、KTV,也会随时随地哼唱流行歌曲,在阅览室谈情说爱。他们会去听演唱会,看足球,大喊大叫,也会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发微博、发微信、刷朋友圈、自拍、搞怪、求关注。他们会看电视剧、看电影,也会做键盘侠、吐槽、骂战、发弹幕。心理快感引而不发,附带伤害不计其数。直到几十年之后,他们要么跟广场舞老太一样,赤裸裸地靠吸食别人的精血维生,要么跟那个唱歌老头一样——瑟瑟寒风中,一个老头用话筒和音箱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唱歌。唱的是几十年前文革时代的歌,“伟大统帅毛主席,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没有伴奏,颤颤巍巍,翻来覆去就那么一首歌。生前没人听,死后只能带进棺材。如果死后还能表达,那就是不朽的证据,会有人心甘情愿地献上自己或他人的生命作为供养。
摄影:Lin Yun Yun(台湾)
注:《新约·约翰福音1:1》一般翻译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最早的古希腊文版中用的是λόγος一字,也就是“逻各斯”(logos)。逻各斯的含义接近“语言”、“话语”,常用在哲学之中,故作者如此翻译。详见:https://goo.gl/fi6j3W(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