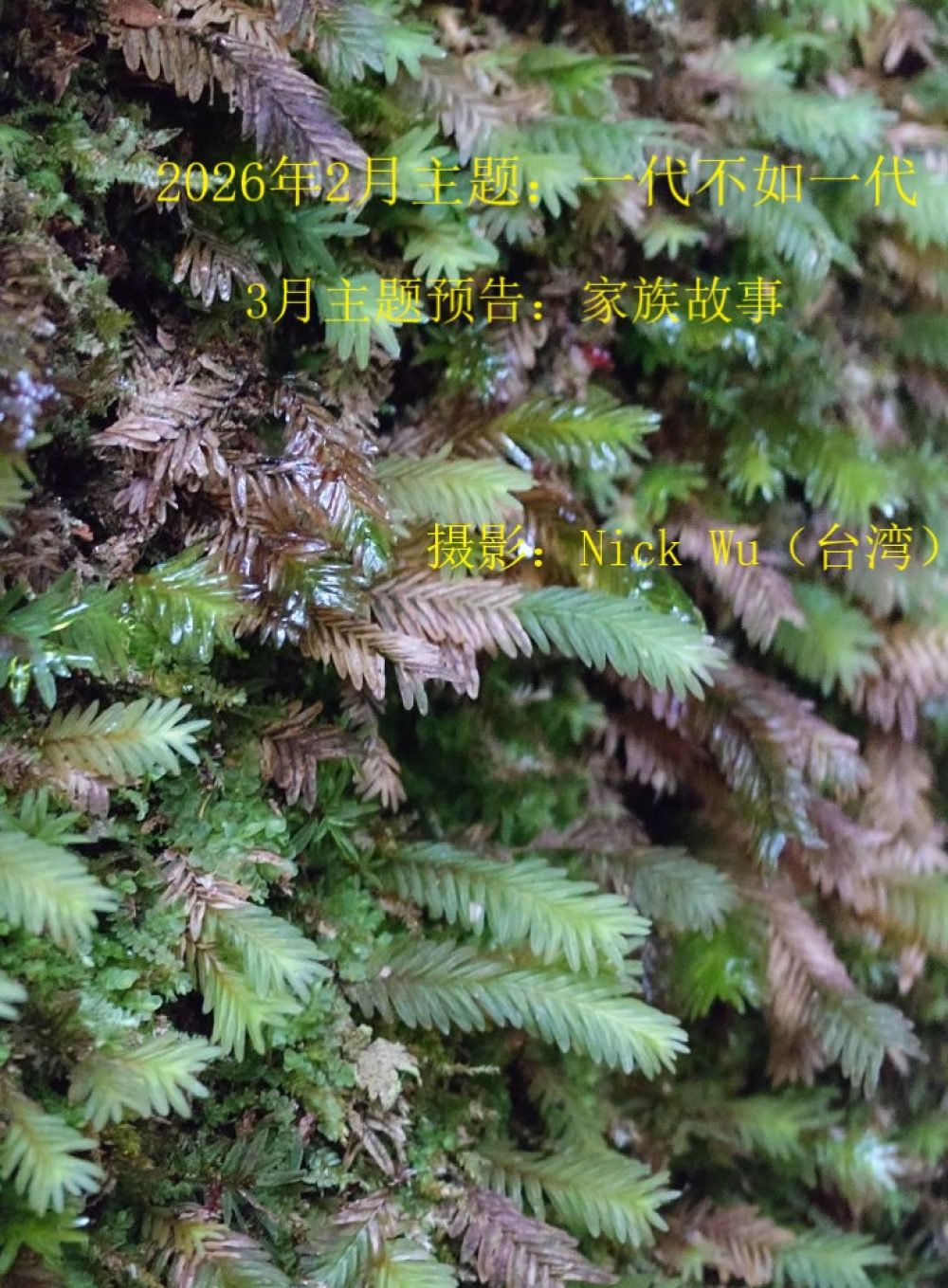卖床垫的推销员说,我们一生有三分一的时间花在床上,理应对自己好一点,所以,买一张跟半辆汽车差不多价格的高科技床垫回家睡吧!我是个知足的人,没沦落到睡在街头已经感觉十分幸福,何况荷包里真的掏不出半辆汽车的现款,只好打消这个对自己好一点的千载难逢机会。
人生中“三分一时间花在睡觉”的说法时有所闻,但是现在还真有人每天睡八小时吗?据《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说,在北美洲地区,二十世纪初的人每天要睡上十个小时,上一代人睡八小时,今天北美成年人平均只睡六个半小时。在这个世界村的时代,至少我身边朋友每天睡六个多小时的人就比比皆是,一点也不稀奇,可见我们之中许多人已经超越了睡八小时的世代,而且和时代脉搏贴得很紧。
这算是好事吗?难说。在古代,天黑了不睡觉还能做什么?那是没有选择的年代。等到祖先们懂得照明后一直到今天之前为止的那一长串日子,睡眠则成了一种选择。世界很纷乱繁杂,生活很艰难无奈,而睡眠提供的正是一种能够抽身而去的短暂喘气空间。于是,我们睡觉去。
不久后,有人发觉睡觉提供不了什么效益,慢慢地越来越多人自动自发缩短睡眠时间,至少我们知道一世纪以来已经从十小时缩短到六小时半。资本主义社会编制的二十四小时不分昼夜的生产、流通、消费流水线,已经像希腊神话里的海妖歌声般,成功迷惑了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自愿放弃睡眠时间而投身资本主义的熔炉,加班、上淘宝败家。
到现在为止,大家对六小时的底线还相当坚持。一旦得知有人超越底线,必是先好言相劝、奔走相告,接着介绍催眠药物、偏方、医生。当事人原本不当一回事,日子一久也被碎碎念得心中不踏实起来。
今天睡六小时半的人,用二十世纪初的眼光来看,毫无疑问是患上严重的失眠症。即使是对上一代人来说,该睡觉的时候不睡,就算不是严重失眠,也多少有点失心疯。不过,反过来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前两个世代的习惯,我们又能说出什么好话呢?这是代沟的问题吗?我觉得是我们这时代的海妖把歌声练得更好了。
有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到美国耶鲁大学继续读中文系硕士,对某位洋教授在任何时间都会马上回复电邮的现象赞叹不已。这位美国教授严重失眠吗?估计不是,否则就没有什么好赞叹了。这一位美国教授之所以被赞叹,在于能够在睡眠时,随时醒过来回复电邮而又保持专业和礼貌。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想一想我们身边的电子产品,这不就是以极低耗电量继续保持机器不完全关机运行的“睡眠模式”(sleep mode)吗?
现在我们对服务业的要求都是24小时不中断的。银行的网页24小时可以处理事务,好!服务热线24小时有人回答疑问,好!购物网站可以24小时买东西,好!若换个立场,当工作狂的老板用电邮在半夜三点发指示,你认为那位马上回复的员工A,还是隔天早上九点回复的员工B,以后晋升的几率比较高?24小时服务好不好?恐怕要看自己是提供服务还是被服务的一方了。
待机模式(standby mode)的年代已经兵临城下,我们极有可能成为一种不再需要(或允许)真正休息的新人类。海明威小说中失眠到握不紧拳头的拳击手,很快就会从悲剧人物转化成一个笑话。海明威如果活在今天,他大概也不会为了失眠而自杀了,睡不着就上网看看地球另一端的股市行情吧!再不然,翻翻FB,回几封电邮、几则短讯,怎么就天亮了?
这个转变是件好事吗?我真的不知道!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