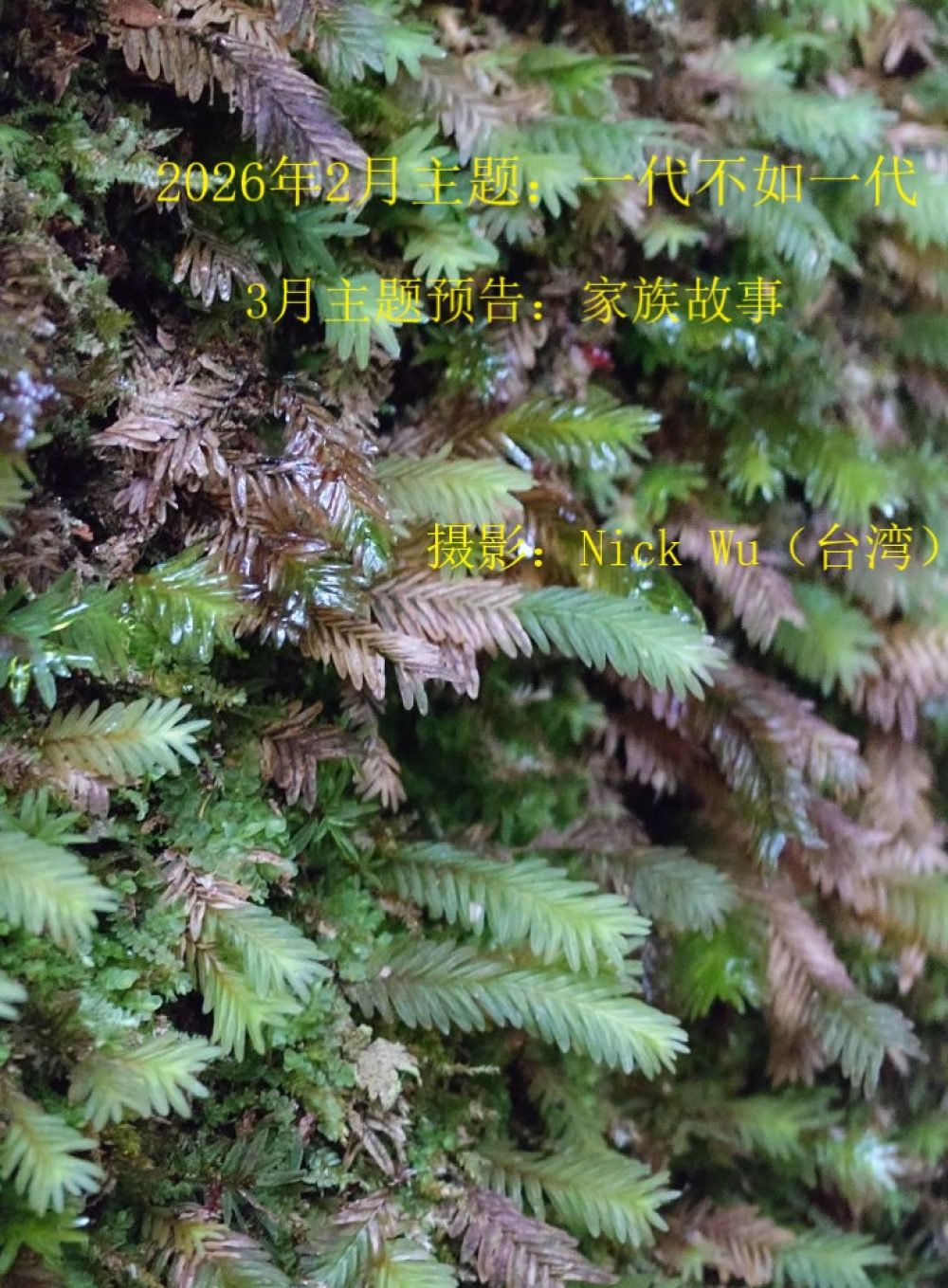法国思想家加缪尝言,真正的哲学问題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这并非肯定或是否定自杀,但多少突出了人的主体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死亡是无法防备的。你也许能预想到100种死去的方式,但最终发生的可能是第101种。不用说交通意外或者安全事故这样的突发死亡,即便你收到一份绝症确诊单,也没人能准确预料丧钟何时鸣起。你也许从不敢相信到接受现实再到寻找出路,直到绝望安排后事,转了一大圈但生命顽强地在这一切之后继续;而另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则没有如此好运,可能完全来不及交待后事就一命呜呼。总而言之,死亡是如此重要,但无论你如何为此未雨绸缪,也几乎没有人能全身而退。而唯一的例外,是自杀。
自杀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古往今来屡见不鲜。所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如荆轲或者谭嗣同;为情为义的,如杜十娘或者祝英台;还有为了理想的,如王国维或者林昭;抑或为了情操的,如顾圣婴、傅雷。除了这些名士高人,还有无数的泛泛之辈,或生无可恋,或畏罪自杀。但不管哪种自杀,都是普通人为自己命运的勇敢抉择。一般说来,只要还活着的人,即便是绝症晚期的病人,也仍抱持一丝生的希望,顽强地多坚持一天,因为明天或许总是新的一天。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毅然决然地自杀的人们是如此地确信明天一定不会比今天更好,或者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走向理想中的模样。这是怎样的一种阅尽沧桑,又是怎样的一种理想主义。这足以令人世间大多数浑浑噩噩苦中作乐的人汗颜。
自杀当然也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对死亡的恐惧构成了人类诸多的情感来源,比如食欲、色欲、感伤、悔恨等等。仔细说来,食欲代表了人类的求生本能,色欲代表了人类的繁衍本能,而感伤与悔恨之类的情感都源自人类对于生命有限性与时空不可跨越的条件反射。简言之,这一切都是生命无法重来的恐惧,也是嵌入人类DNA的本能,让我们不顾一切去逃避死亡。绝望者用各种宗教的谎言来麻痹自己,不屈者则寻找各种长生不老药来延缓死亡。只有自杀,是一种与死亡的正面对峙,对求生本能的顽强超越。虽说所有的人类审美归根结底都建基于善待生命,而自杀也有违基本的生命美学,但生命的本质更是追求自由、爱与尊严。若生命确定失去这些价值,那么其同时亦不再具有审美价值,毁掉它反而是一种善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席勒说“生命不是人生最高的价值”,而自杀实则体现了更高的生命价值——以个人之死去召唤人类物种整体环境的改善,以为人类物种的延续增添一丝机会。
与神话传统中美化英雄自杀不同,今日的医学把大部分主动自杀的人归因于抑郁症发作,进而通过神经科学解释为脑神经损伤,与阿尔茨海默病、渐冻症等病症一概纳入“神经病”的范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Robert
Sapolsky更是一直宣称自由意志并不存在,人类的一切行为可以从客观的生物进化过程中找到依据,而具体到每个人的行为,也不过是他/她先天后天诸多要素的集合。所谓的自由意志,不过是科学还未够发达之前人类所无法解释的内在力量。无独有偶,今天几乎所有的实验神经科学都在试图将人类行为与特定神经元区域的决策联系起来。这些客观决定论的观点从生物微观层面消解了自杀这种自主选择的能动性,却与社会宏观层面对自我牺牲的礼赞截然相悖。比如飞蛾扑火,虽然本质是一种诱杀或者盲从,但我们仍然愿意相信这是向光明的主动奔赴;又如舍己救人,我们也总愿意美化其为无私奉献,却无视了这样的事实:少有人会在救人之前做好利益权衡,并决心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的根本死因其实是脑神经受限于眼前危急情势而对可能发生的救人风险预判失误。相似地,“我以我血荐轩辕”也可能是一种对人类共同体一厢情愿的误判,所有的自我牺牲不过是满足了大脑的文学想象。
当然也不用等到科学家们来掀桌子,后现代哲学家们早已经将传统的“我”革了命。自从“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把“我”这个主体创世以来,并经由康德等人以主观统摄客观,达到唯心论顶峰;而后物极必反,在尼采、马克思那里物质肉身成了更重要的实体(李泽厚语)。直到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家们甚至直接否定了主体的可能性,人不过是被知识与权力随意摆弄的躯壳,主体因此早已消亡。这简直与后来居上的科学家们殊途同归。换言之,在我们自杀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把“我”杀死了。那么此后的自杀,还有什么审美价值呢?这杀掉的“自己”又是谁呢?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死亡
- 上一篇文章链接:父母是“三等”公民吗?/徐嘉亮(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