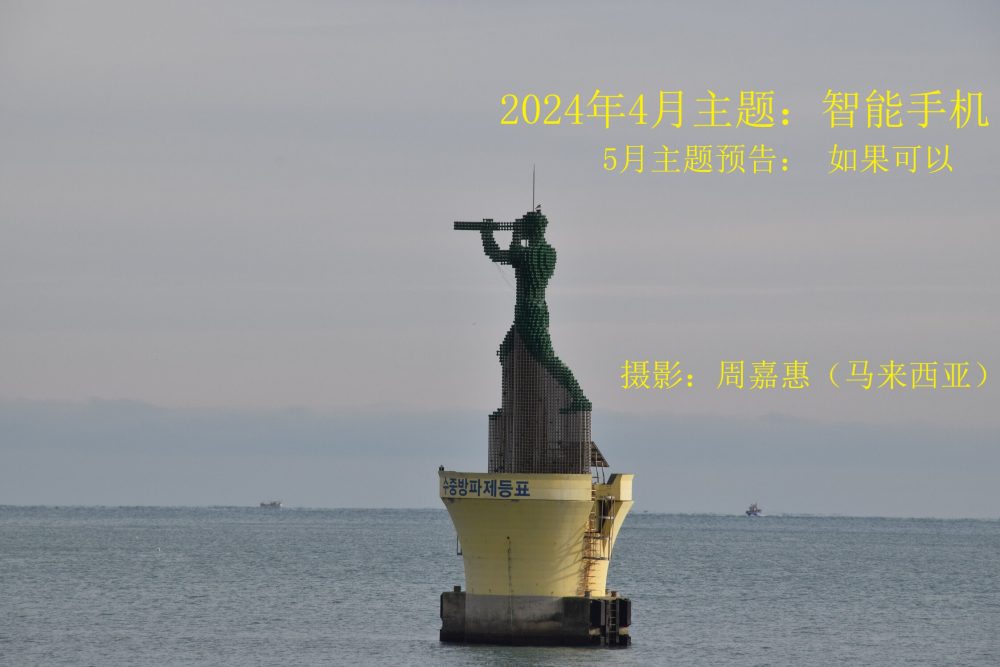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源生于1948年图灵提出的Intelligent
Machinery概念,起起伏伏发展了数十年,经历了数次浪潮,以1997年深蓝与国际象棋大师的人机大战渐渐引起关注。然而当时人机大战互有胜负,依赖强力穷举法的人工智能可说是仍处于襁褓阶段。进入21世纪后随着计算机算力的突飞猛进,以及深度学习等新算法问世,让人工智能应用得到长足发展。在2017年Alpha Go轻松击败所有人类围棋顶尖高手之后,人工智能成功出圈,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热点,也几乎一跃成为所有学科的显学。计算机科学等理工学科自不待言,人文学科也一拥而上,人工智能伦理学、人工智能艺术学、人工智能哲学,甚至包括荀子思想对于人工智能的启示、人工智能与老子的关系等等,不一而足。
众多学科的介入动摇了人工智能的定义。原本仅限于计算机学科内部的寄望于制造出更聪明的Thinking Machine的人工智能方向,被普罗大众文学想象为可以超越人脑的超级智能生物。认知学科迫不及待地试图为人工智能指明发展意识的步骤,伦理学家们则“理智”地指出人工智能的伦理学守则。而这些都让脑科学家们大呼无奈,毕竟人类目前的脑学科发展水平连大脑的基本运行逻辑都还远远未能摸清,如何可能制造出近似人脑甚至超越人脑的物种呢?对于基本的意识、情感、意志这些重要概念,哲学、计算机科学以及脑科学都未能统一认知,所谓的人工智能,又有多“智能”呢?
还是务实的计算机学家们为我们澄清了人工智能的误解。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只是基于图灵机的二进制原理,主要在封闭性准则下通过设计算法来帮助解决人类日常问题的一种辅助手段。换句话说,无论Alpha Go可以多么轻松地战胜人类棋手,它从来不知道它在从事一种棋类运动,它的本质仍然是计算机在完成二进制运算。人工智能的构成原理与以人类为代表的哺乳类动物大脑发育大相径庭,无论如何难以发展为一种类人脑的存在。好比人类为了飞翔,发明了飞机,但飞机飞行的原理与鸟类并不一致。若是去一味模仿鸟类,人类恐怕永远发明不出喷气式飞机或者螺旋桨飞机。因此,人工智能更准确的名字也许应该是“辅助智能”而非“类人智能”。对只知计算的机器施以人类的伦理、社会法则,无论这个作为工具的机器能发展出怎样的“智能”,仍显得牛唇不对马嘴。
人类对作为人工智能参照物的大脑自身的研究仍然迟滞不前。目前的脑科学大致认可了大脑中的神经元是主导大脑作出判断的基本单位,但限于技术伦理限制,无法对于正在运转中的大脑作出更加深入的探索。全世界都在等待着脑科学的迎头赶上。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脑科学能证明人类的所有活动其实不过是基于神经元的量子计算结果,所谓的情感、意识也都是计算产物的表象。如果真有这么一天,那么机器与人脑的原理或能基本打通,我们方能见到真正的人工智能的诞生。只不过与其说它是机器的智能化,不如说它意味着人的彻底工具化。工具理性一统天下,数代人孜孜以求的人工智能伦理学最后无异于一篇机器运行守则。
摄影:Clement Poh(马来西亚)
主题:突围
上一篇文章链接:2434/练鱼(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