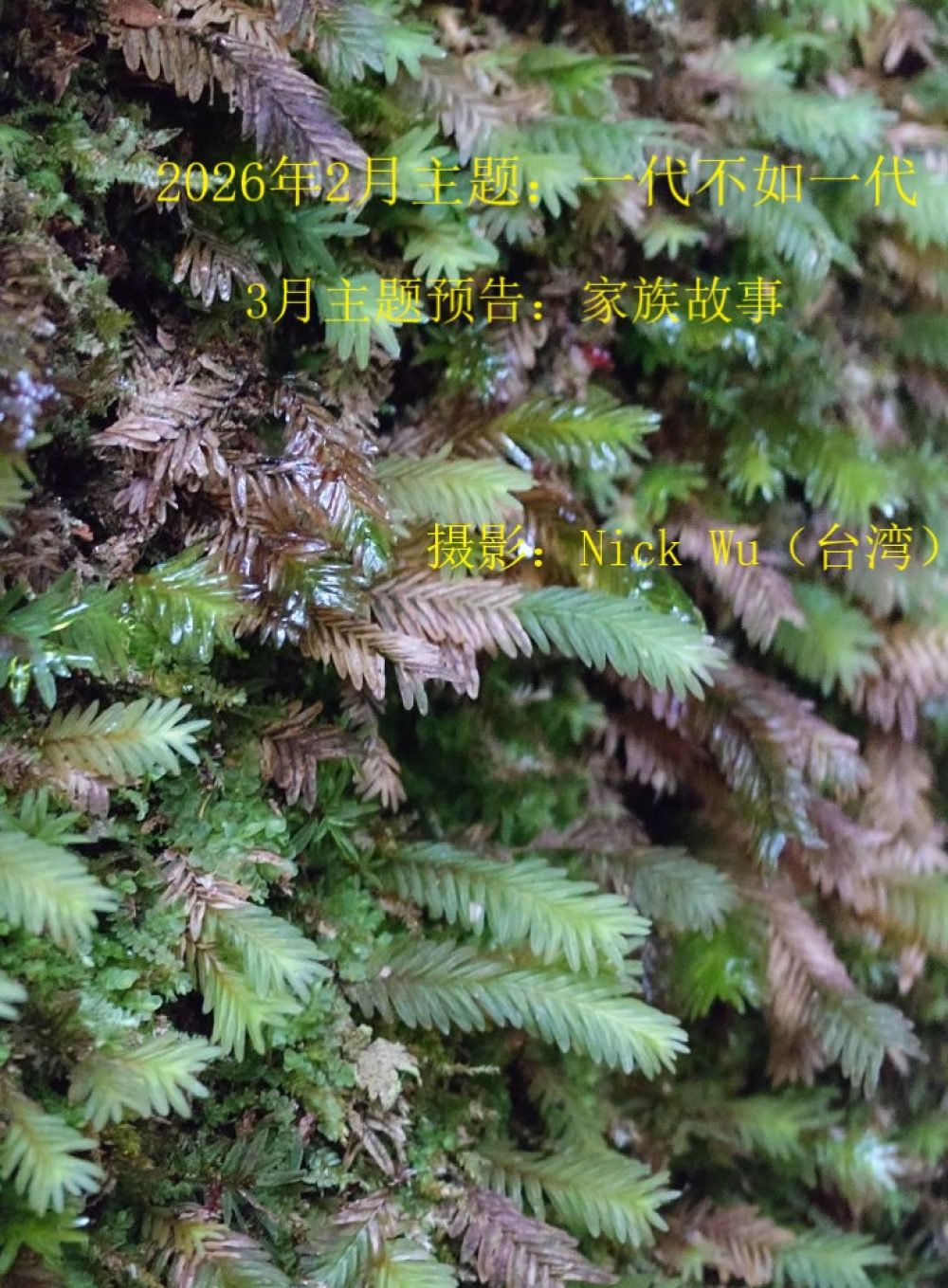小学时代,记得有一天醒来,尚恼着课堂的测验,忽而得告冬菇去世,休假一天,一时若脱钩之鱼,不妨熟歇。谁冬菇啊?后来从课本才懂得东姑乃国父也。国父在默迪卡广场领众举拳,响彻云霄地喊了三声“默迪卡、默迪卡、默迪卡”,已经成了经典短片,每一年时间到了,如唱盘回唱,而我,尤其喜欢国父鼻梁上驾着那副厚重的黑框眼镜。
默迪卡,为什么非得喊三声?从来没有人问,老师解说这三声后,正式宣布了马来亚的独立。这三声默迪卡,声声慢、声声重,情真意切,确实感人,这致使我对影片中的主角一直有种莫名的喜欢。
可惜,一直到后来我才理解,喜欢某一些事物或人,往往源于误解。实话说,这世上的事物,理解之后或许能多一些宽和、少一些期待,但喜欢,往往是说不上了——更何况对象是一个政治人物。
东姑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应该是从英国人那里求得了马来亚的独立。然而,他一辈子所坚持的种族特权,以种族为政党基础和理念,不啻为一种魔咒,让他在历史上的身影愈变愈小,直到让人俯视的角度。
独立前的马来人,和现在很不一样。纵使依然淳朴善良、简单,甚至有点闲散的懒惰和愚昧;现在的马来人,经过五十年的政治教育,更多了份由根植于自卑的民族的骄傲。无论当年的东姑乃至马哈迪的时代,大概觉得保护和捍卫马来民族是他们的责任,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一穷二白的子民,加上骨子里的憨直,哪个父亲不是那么恨铁成钢的?
东姑一辈子结了四次婚,当中只有一个是马来人,亦无所出。除了第二任的英国房东,其余两人都是华人。东姑的孩子都有华人的血统,然而,在政治上他的底线还是紧紧系着他的民族情结。那个年代受英国教育的这些马来人,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对自身的认知确实有种时代的烙印。我想,虚无主义在这种语境下,多少显得有点超脱和有益于反思——无论如何,马来人的热血和任何可以操弄的主义有种化学上的作用,现在几乎成了一种政治必要了。
简言之,对于马来人连东姑都是没有十足信心的,所以尽了力去保护。后来,1963年与新加坡、婆罗洲成立了马来西亚,这种坚持也从未改变。或许当初并未意识到政治上的威胁,建立马来西亚是出于一种理想,如李光耀谈及新马分家时感慨落泪所说,其一生坚信于新马的合并,因为无论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我们都紧紧相依。
在这种氛围下,李光耀走进马来西亚的舞台。他能言善道,唇枪舌剑,用马来文和英文跟这些马来精英辩论,弄得大伙儿焦头烂额、灰头土脸的。李光耀从弹丸小国合并而来,即挟带了大量华人——近半的马来西亚人民当时是华人,本身又一愣头青,不管当家的想法,就是要全民公平,强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种前瞻的视角和理解是进取、积极,也极不识时务的。我觉得强悍如斯者,能一路走来创造出这么璀璨的小国,就人类生存史上也是奇迹。他在和邓小平的对话中有谈到过,像他这样的人物如果出生在中国,或许能活到老去就算了不起了。确实,人类有很多天才都是死于一般暴民和庸才的手里,躲得过去这些攻击,出生在小国,和这么一群小人物打交道而得以保命而一展手脚,多少是命运使然。
东姑的集团开始感觉到除了民族使命以外的其他意义了。这是一种纯粹政治的斗争。李光耀带来的威胁是巨大的,他的理念是进步的,他的言辞是不可斥驳的,他是该死的。东姑作为马来人的局限显露了,无论是捍卫马来人或他的政治集团的地位和特权,他决定停止这一切的麻烦。通过压倒性的会议,他们一致通过把新加坡撵出门外。那会议并没有任何新加坡的代表受邀出席。这当中没有任何协商和沟通的意愿——这再一次、最后一次说明了,当家说了算。李光耀和东姑同是英国留学生,法律系毕业的,前者是剑桥法律系史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后者考了几次凑合毕业了。当然,以成绩取人未免肤浅,然而,从种种行迹上来看,确实是有一定本质上的差异。
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脱离了。这不是东德和西德的分离,也不是大陆和台湾的分离。这绝不是不同政治理念的分离,而是政治水平不同的分离。从此,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水平来发展,不同的议题来发展,相同的人民,相同的土地,越一个海沟,人民自由来去,但是我们的历史都回不去了。
而今,这两人都仙逝了,任由后人评说。李敖在他的节目中有评论过,他不喜欢武侠小说,觉得这东西飞檐走壁,男女情长,都虚妄的,而且格局太小。他觉得民族大义这才够谈。然而,我觉得李老先生越老越激进的思想也有其时代的局限了,民族大义只是一种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工具,如东姑一样,套着了就一直解不下来,反倒成了囚牢。脱了一枷锁又戴上另一个,算不上聪明吧。李光耀,格局够大了,能生长发迹于小国中,是新加坡的福气,亦是他个人的福气。
(照片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