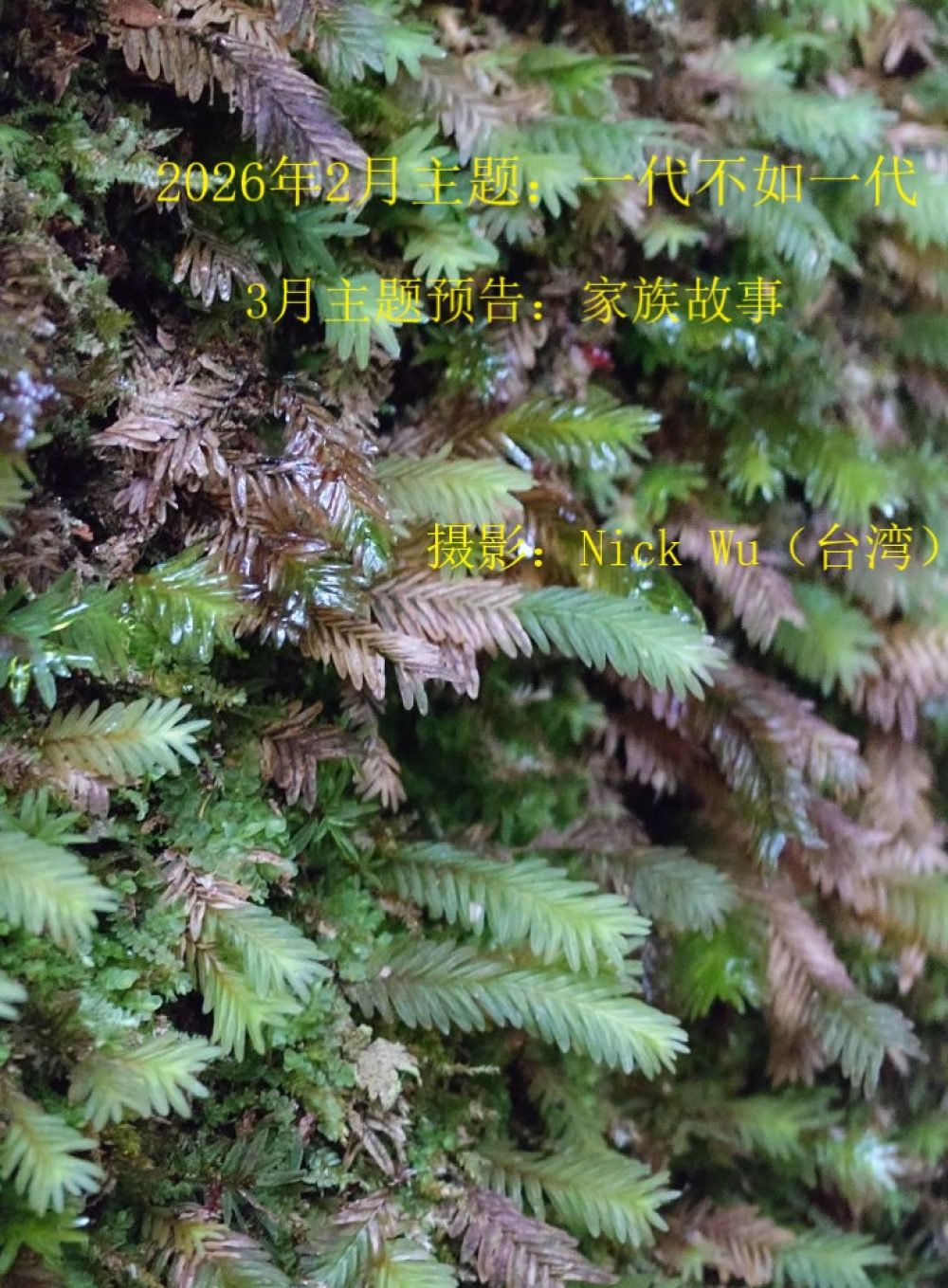放眼当世,物欲横流,矫假泛滥。我们相当一部分的新生代,学历越来越高,学力却日趋浅薄;学问的精细度越来越牛,思维的理性化和胸襟却比蹇驴好不到哪里去。在非黑即白,各自旗帜鲜明、立场尖锐地为自己属意的政客充当马前卒的激情之中, 在民粹主义、糊弄是非、积非成是以及严重撕裂社会的潮汐里头,若要呼吁公众学习理性思维并大谈“哲学”,倒显得有些语焉不详、神经错乱了。
风旋雨啸,浮尘热恼,傀儡喧闹。放眼寰宇,当世只有“一极”,那就是美国,说确切些,那只是“美国利益”。许许多多高呼“民主”、“自由”或“爱某某”那歇斯底里的呐喊之中,面对的更是意义思维的苍白。于是乎,民主一词需前缀个“真”字,自由一说务必添上“正”字,翻江倒海,蔚为奇观,荒谬之极。再看看巴勒斯坦加沙地区许多无辜的贫民和孩童被以色列导弹击中,在悲号、恐惧和鲜血淋漓的痛诉里,彼时彼刻,我不知道那些一向拥抱山姆叔叔大腿,亲昵呼叫“美国爸爸”的所谓个人自由主义者,是哭,是笑?他们为何集体噤声失言了呢?
哲学,有活生生的“生哲学”和鹦鹉学舌般的“死哲学”两种。个人认为,学习哲学不是学习或者紧紧拥抱什么教条、名相、说词、道理、至理或普世价值,当然,不是“一贴膏药走遍天下”,更不是千秋万世的终极真理。这是说,哲学并非一个名词,不是一个“东西”,更不是那所谓的一招半式。那是枯死的哲学。
现代相当一部分好学者学习哲学,熟记某名家某氏所言,据此睥睨天下,单凭其三招二十一式的快刀把式,自封江湖盟主。当年我念台大哲学系时,最害怕并忌讳和某些“自视甚高”的同学论学。他们兴许读过诸如康德、黑格尔或沙特等名家的部分著作,于是乎一叶障目,处处批评并否定别人的看法。他们岂知所有的学说及思维模式,若一旦成为体系,那就一定存在它的缺点、刻意歪曲之处以及致命的死穴。
读了多年的哲学,有三位教授的三句话充分地启发了我。迄今,由于现实生活的煎熬,我时而忘记了诸多的哲学名词,然而,哲学思维依旧在我的血液中流淌,偶尔不经意地伴随着雄浑的掌风推将开来。
其一,刘福增教授曾说:近代哲学不是要追求什么,更不是要搞懂什么,近代学者所努力的,只不过努力尝试把一些概念弄清楚一点而已。我认为,“哲学”是一个动词,切切不是一个名词。自从古希腊、先秦诸子以来,人间许多睿智聪颖的脑袋投身于哲学思维,然而,时移世易,我们不能简单的刻舟求剑,更无法循表夜涉。用明代汤显祖的话来说,“今昔异时,行于其时者三:理尔、势尔、情尔。以此乘天下之吉凶,决万物之成毁。作者以效其为,而言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有理至而势违,势合而情反,情在而理亡,故虽自古名世建立,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语人者……嗟夫!是非者理也,重轻者势也,爱恶者情也。三者无穷,言亦无穷。”(《弋说序》)
其二,关永中教授在叙述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他在念完哲学博士之后,本以为可以穷理尽性,然而他发现许多人在尝试推开哲学的最后一道大门的时候,发现那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关教授是个执着而美善的知识追求者,后来,他来到比利时鲁汶大学,再重头念起神学。他觉得,他在神学那里找到了开启问号的钥匙。哲学,志向甚大,一向自诩为寻找万事万物的终极道理,却经常迷失于道理之中。毋庸置疑,这精神是可敬可赞叹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正是怀德海的“流动”吗?(哈!这攀附,并不究竟哦。)
其三,逻辑学教授林正弘在逻辑学的第一堂课上告诉学生们说:有一天,你们可能忘记了所有逻辑学的演算公式和方法,然而,只要你认真地跟着我学好这一学年的逻辑学,你的思维肯定超越一般人。细细思忖,20多年后的我,翻开逻辑学课本,已经看不懂,也不会演算了。每一回翻开那犹如电话簿般厚重的逻辑学原理,我都不自觉地会心一笑。
红尘热恼,说哲学,其实,也蕴涵了被批判的命运。说与不说,其实没什么分别。我们习惯于辨析和区别,近些年来,我倒喜欢思维“等同”或“无区别”。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得即是失,失即是得;说就是不说,不说就是说;笑不异哭,哭不异笑……(像崔永元那样,笑起来就像是哭着似的!)
“十字街头葛藤露布”,在禅思里,露就是不露,不露就是露,“无住者,非无所住也,乃不着于住”(《金刚经》序言)。唉,到底我现在是露还是不露,住还是不住?尘世业障系缚之身,不如“出门一笑大江横”吧!
(摄影:淡水河边)